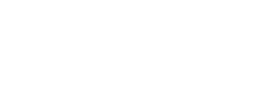歡迎來到正觀雜誌社的網頁,我們定期出版的《正觀》,是一本佛教學術研究期刊,懇請十方大德以及專家學者共同支持,也歡迎捐款助印。若您使用本網站撰寫論文或學術研究,請加註說明。歡迎訂閱電子期刊。
| 期刊名稱:正觀 出版者:正觀雜誌社 出版地:南投縣,台灣 出刊頻率:季刊 創刊日期:第1期,1997年6月25日 |
Name: Satyābhisamaya Publisher: JhengGuang Magazine Place of Publication: Nantou hsien, Taiwan Frequency: Quarterly ISSN: 1609-9575 |
正觀雜誌目錄(1-101期)
-
2009-03-25 出版第48期
-
Bhikkhu Analayo(無著比丘)原著•蘇錦坤 譯 註釋書對阿含經文的影響
本文意圖顯示部分阿含經文受到來自註釋書的概念與見解的影響,這樣的影響不僅發生於漢譯時,而且也可能已經發生在口誦傳承時,這些影響已經成為印度語系原文的一部分而被翻譯成漢語。
本文的第一部分,我檢校了一些與其巴利對應經典不同的阿含經文,有一部分此類經文顯示了這個差異與巴利註釋傳統十分相似,而給人這樣的顯著印象,這些我們所考慮的經文可能已受到古印度註釋傳統所影響,這個註釋傳統與現存的巴利註釋書的解釋相似。為了顯示在這些例子所觀察到的模式並不限於阿含經文,接著我以一些巴利經文的例子顯示此一特性。綜合來看,這些例子則意涵著註釋可能在口誦傳承的時期就已經影響了所註解的經文,這樣的結論會與諾曼 (K. R. Norman)「註釋書與經典為分開來傳誦」的建議衝突。如果註釋書與經典分別傳誦,會使得前者影響後者的情況變得較不可能發生。因此,在本文的最後部分我謹慎地審核諾曼的意見,而得到「註釋非常可能與經文一起傳誦」的結論。 -
Bhikkhu Bodhi 原著•蔡奇林 譯 《佛陀的話語:巴利經典選集》總導讀
【翻譯說明】
本文譯自Bhikkhu Bodhi(菩提比丘) 2005年編譯出版的In the Buddha’s Words : An Anthology of Discourses from the Pali Canon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一書的 “General Introduction”(頁1-15)。
菩提長老此書,選編了巴利尼柯耶中的重要經文,並將之安排組織成一個次第分明的「修學架構」(道架構),讓學習者面對龐大的巴利經典群,不再不得其門而入,甚至望而卻步。誠如長老在此書的序言中所說,它就宛如一張「穿越叢林的地圖」或是「渡越大洋的船舶」。循著它,「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將不再遙不可及。
此文包含三大部分:一是,揭顯法教的架構,介紹上述「道架構」的概貌和旨趣。二是,尼柯耶的起源,介紹巴利尼柯耶的來源和性質。三是,巴利聖典,介紹巴利三藏的組織、內容、和重要性。這些內容對於巴利佛典的學習者,具有很好的入門指引作用,因此將之譯出,提供讀者參考。
譯文中小方括弧“[ ]”中的數字,是原書的對應頁碼;大方括弧“﹝﹞”中的文字,則是譯者所添加,以使譯文更加明白或順暢。譯文最後,附上了文中所用到的「縮略語」和「引用書目」。
本文的翻譯,承蒙菩提長老慷慨提供授權,特此致上誠摯感謝。正觀雜誌社的編審委員,細心審閱本篇譯文,並惠賜許多寶貴意見,也在此申致謝意! -
蘇錦坤 撰 《雪山夜叉經》──巴利經典與漢譯經典對照閱讀
本文比對下列經文:《小部尼柯耶》《經集》的第一章〈蛇品〉第九經《雪山夜叉經》(Hemavata Sutta ),與《雜阿含1329經》、《別譯雜阿含328 經》、《義足經》第十三經《兜勒梵志經》前半段之《雪山夜叉經》相關的經文,和《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第四品〈夜叉神品〉等四部漢譯經典。本文的比對,顯示上述漢譯四經在故事框架、偈頌次序與偈頌數量均與《經集》之《雪山夜叉經》不同。本文判讀《別譯雜阿含328 經》的部分偈頌詩句錯置,並且嘗試「復原」此經偈頌的「適當詩句次序」。
巴利《經集》《雪山夜叉經》有些版本有重複的 163, 163A,163B 偈頌,有些版本則無此重複,漢譯的《雜阿含1329 經》與《別譯雜阿含328 經》在此提供了較為合理的解釋。
最後,本文就對照閱讀所顯現的差異,依「緣起故事的有無」、「《別譯雜阿含328 經》偈頌詩句錯置的現象」、「法義問答的偈頌與其他經文相同」、「巴利《經集》《雪山夜叉經》重複的偈頌」與「翻譯用詞的一致性」五個議題作探討。本文也提出「《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出自闇誦」的假設,以待進一步檢驗。
本文經過偈頌比對,認為純依偈頌而言,《別譯雜阿含328經》比較接近《雜阿含1329 經》,《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夜叉神品〉比較接近《經集》《雪山夜叉經》;支謙所翻譯的《義足經》第十三經《兜勒梵志經(部分)》則比較接近《別譯雜阿含328 經》與《雜阿含1329 經》。 -
釋如恒 撰 《大乘起信論》之止觀修持──依「修行信心分」之「止觀門」
-
釋智學 撰 中國佛教的懺悔觀
吳越國高僧永明延壽(904~976)曾經力行實踐法華懺、方等懺等懺法,除此之外,他的著作群中也出現了許多與懺悔有關的專門性語詞。甚至在記錄他的修行生活的《智覺禪師自行錄》中,也詳細載錄了他力行實踐的懺六根罪、五悔法等懺悔法門,再加上延壽非常重視戒律,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延壽對於「罪」和懺悔的理解,以及他的修行者自覺。
在本稿中,筆者意圖以呈現在延壽的傳記資料及其著作群中的「懺悔」用例為中心,而進行論述。但是,由於「懺悔」在中國並不是僅只受到佛教體系的重視,而是在中國傳統裏也從相當早的時期就與罪惡的意識、悔過、齋會等相連結,廣泛地受到重視,並付諸實踐。所以筆者擬以三項內容,即(一)懺悔的語義、語源問題,(二)懺悔的典據及儀式化的問題,(三)永明延壽的懺悔觀,作為考察的線索。 -
曹仕邦 撰 《付法藏因緣傳》真偽的疑問
-
-
2008-12-25 出版第47期
-
無著比丘 原著•蘇錦坤 譯 誰說的法、誰說的話──巴利與漢譯經典關於說者的差異
-
呂凱文 撰 重讀佛教「王舍城結集」
「王舍城結集」一直被視為是解讀佛教歷史的第一手資料,但是不同傳本內容的出入,卻使得研究者對於它的史實真偽問題起著諍論,從19世紀末開始歷經百年仍有人翻案。然而,若我們檢視不同部派傳本在王舍城結集敘事的差異,就不能不面對它與真實歷史的差距中,隱含著許多表述者等的觀點和詮釋之事實。在此思考上,首先,本文從學界歷來的王舍城結集研究成果出發,重新反省這種文類的特質。進而,將討論範圍縮小在「王舍城結集」本身與「小小戒可捨」事件上,不僅批判地檢討學界對此事件的解釋,同時也比較各種傳本敘事內容的同異。最後,在逐層逐次解讀各家觀點與不同傳本的詮釋性格之過程中,我們將揭露這些詮釋性格中隱而未現的「知識/權力」共構關係,也藉此反省王舍城結集的故事。 -
許明銀 撰 章嘉宗義書〈中觀派章〉漢譯(三)
-
孫致文 撰 上海博物館藏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上》寫本殘卷的研究意義
-
萬金川 撰 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諸法言品第五》上博寫卷校注
-
德妙佛學中心2006年圖書目錄
-
-
2008-09-25 出版第46期
-
黃纓淇 撰 聖樂(ariya-sukha)之研究
在初期佛典之中,提及了一組「聖樂」(ariya-sukha),是佛陀常常勸勉弟子們應當多多親近與修習的。此組「聖樂」,指的是「出離樂」(nekkhamma-sukha)、「遠離樂」(paviveka-sukha)、「寂滅樂」(upasama-sukha)、「正覺樂」(sambodha-sukha)這四者。此「聖樂」是佛教裏所認為無過失,助益於修行、解脫之樂,而鼓勵應當多多修習的。然而,此組「聖樂」的內容,在經論當中的說明並不一致,有的解說此四者皆屬於「禪定樂」;但是也有指出此四者分別包含了「禪樂」與「解脫樂」,甚或是其他種類的樂。究竟此四種聖樂實際所指涉的內容為何,以及為什麼經論的解釋會有不一致,成為了本篇研究討論的主要焦點。然而,若「聖樂」中的某些成份真的包含「解脫樂」,這樣的「樂」究竟是怎樣的樂呢?描述解脫的「涅槃樂」真的是一種「樂受」嗎?「涅槃」之「樂」有什麼特質呢?這些都是本篇文章所將要一一探討的。 -
康特 撰 中觀學的時間觀
本論文主旨在於探討中國大乘佛教中觀學以龍樹與僧肇為主的時間觀。 龍樹於《中論》中主張「三世無實有」的觀點,而僧肇在《物不遷論》中則成立「三世無來去」的觀念。筆者將論證,兩個觀點其實不相違背,都以空義為依據來發揮時間在大乘佛教救度學範圍內的重要性,但脫離佛教救度學範圍之外無時間可談,也無法成立一個超時間的觀念,與西方天主教Augustinus由存有的角度上所研討的時間觀完全不同。筆者也將進一步探討西方佛學研究關於該議題的看法,並且對此予以評論。 -
沈海燕 撰 《法華玄義》的成就
作為天台佛學的根本教義,智顗的《法華玄義》在“天台三大部”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故此,若能瞭解這一巨著的成就,我們便能深入智顗博大精深的圓融哲學思想體系。本文從三個方面闡述了智顗這部著作的成就:一是有關《法華玄義》的文本結構和理論框架,二是有關智顗建立其思想體系所運用的方法和技巧,三是有關智顗思想體系的內容及其佛教哲學形成的過程。 -
黃英傑 撰 藏傳佛教他空見研究小史
-
德妙佛學中心2005年圖書目錄
-
-
2008-06-25 出版第45期
-
蘇錦坤 撰 《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
本文列舉攝頌的功能,並且檢視了《別譯雜阿含經》與其攝頌的對應關係,這兩者顯示相當程度的一致性,但也呈現了不少差異。本文嘗試將《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對應到相當的各部經典,詳列兩者之間的差異,並且探索攝頌所顯示的特點。 -
吳汝鈞 撰 佛性偏覺與佛性圓覺(下)
-
白金銑 撰 《水懺》與〈水懺序〉之關係三論
本文透過敦煌文獻、佛教文獻與人物史傳,處理學界、佛教界對《水懺》與〈水懺序〉間一直混淆不清的三個問題。其一,《水懺》的主體內容,早在六世紀時已含備在敦煌本二十卷《佛名經》中,並不是〈水懺序〉中所說的唐代悟達國師(知玄,811~883A.D.)所撰。其二,《水懺》的主體內容(三障懺悔文字)是印度大乘佛教「以水洗瘡」的緣起療心之懺悔譬喻,其根本方法是眾生須以緣起的「慈悲心力」、「悲喜心水」進行懺悔,不是依賴〈水懺序〉中迦諾迦尊者的「三昧法水」。其三《水懺》與〈水懺序〉其實是兩篇截然不同、各自獨立的懺悔文字,不可勉強合一。亦即,六世紀時的《水懺》,不等於十五世紀神異化後的《三昧水懺》,若勉強將二法合一,則將嚴重誤解古德撰寫《水懺》之初衷。
-
-
2008-03-25 出版第44期
-
蕭玫 撰 《入楞伽經》之「成自性如來藏心」──論唯識思想影響如來藏之一端
後期的如來藏思想,在瑜伽唯識學派的影響之下,增添了唯識學的語彙並汲取了唯識學的義理,從而拓廣並深化了「如來藏」的義涵。見諸《入楞伽經》的「成自性如來藏心」一詞──意謂成自性(圓成實性)是如來藏的核心要義──不唯串綰了「成自性」與「如來藏」這兩個分屬唯識學派與如來藏學的重要術語,同時也表現出以唯識思想詮釋如來藏的義理傾向。本文藉由分析「如來藏」含義的發展與《入楞伽經》中「成自性」的內容,說明在唯識思想的影響之下,「如來藏」義的重心由「能證之智」進一步向「所證之境」過渡;而如來藏義的涵賅範圍,亦由「如來之智」進而拓展為「境智一如」。 -
吳汝鈞 撰 佛性偏覺與佛性圓覺(上)
-
萬金川 撰 佛典漢譯流程裡「過濂渡性文本」的語文景觀【第一部】譯經文體、譯場組織與譯經流程
-
沈劍英 撰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研究(下)──淨眼論現量與比量
-
王璞 撰 《紅史》考述二則
藏族歷史名著《紅史》載有兩段鳩摩羅什和道宣的事蹟,說法卻與漢籍有所差異,以漢、藏文相關史料為依據,引入同情視角對之進行細緻考述即為本文的主體。 -
蔡耀明 撰 生命哲學之課題範疇與論題舉隅:由形上學、心態哲學、和知識學的取角所形成的課題範疇
本文的工作要項,在於就生命哲學,按照哲學的形上學、心態哲學、和知識學這三門學科,規劃成三個探究的範疇,進而就每一個範疇,設置若干重大的課題類別,並且提出一些論題以為例示,然後選擇關鍵概念或當中的一些論題,發而為初步的思辨與論理,使生命哲學在學術的運作,一旦問及可以打開哲學探究的哪些範疇,有哪些重大的課題,以及可以鑽研哪些論題,便可據以形成稍微完整的概觀。
在論述的行文,透過如下六節,成為以界說、釐清、課題、論題、思辨、和論理交織而成的架構。第一節,「緒論」,開門見山,帶出研究主題,並且逐一交代論文的構想與輪廓。第二節,「營造生命哲學」,從基礎的工作做起,包括界說生命,界說生命哲學,區分課題和論題,借用哲學的分支學科設置探究的課題範疇,以及強調論題的提出在哲學運作的重大功用。第三節,「就生命展開的形上學提問」,主要的課題,座落在關聯於實相所形成的範疇;至於提出的論題,至少可分成八類,依序為有關生命實相、生命目的、點狀意象、歷程意象、歷程環節、生命形態的類別及其本性、生命本身之品質、以及世界系統的論題。第四節,「就生命展開的心態哲學的提問」,問及心態和生命的關係與關聯,死亡之於心路歷程,心路歷程之於靈魂或自我,以及心態之實相和生命之實相之間的平等性關係。第五節,「就生命展開的知識學提問」,整理成四類的論題,分別為有關認知生命和論斷生命、認知與生命、知識與生命、以及生命之意義的論題,並且特別就生命之意義展開課題與論題的反思。第六節,「結論與展望」,總結本文的要點,並且展望後續相關的探討。
本文至少在如下三件事項,力圖改弦更張,和尋求突破,因此可視為研究和論述上的微薄貢獻。其一,生命視野的極力拓展。以生命歷程、生命世界、和生命實相,撐起生命視野的格局;不把眼光只侷限在人生、生活環境、本土、和所謂的人類特質之類的範圍。其二,研究方法尤其是研究視角的調整。(a)為了更為適切打通生命歷程的理路,儘可能調整為歷程式的、動態的視角,而不是緊緊守住存有概念,或製造出來的實體觀念,終歸淪為被語詞綁死的靜態想法。(b)為了更為適切開啟生命世界的理路,儘可能調整為多重向度的視角,而不把日常經驗或物質科學當成唯一且全部的向度。(c)為了更為適切彰顯生命實相的理路,儘可能調整為空觀、不二中觀的視角,並且善用否定詞,而不是由於指稱詞的借用,就自動掉入死板板認定事物的窠臼,也不是由於相對概念在思辨或論述的運用,就輕易掉入彼此區隔或分立二邊的困局。其三,就一些課題的構成,尤其是生命之目的、生命之意義,進行哲學的反思,以幾乎是發前人之所未發的姿態,一方面,避免誤觸許許多多可能深陷泥淖的機關;另一方面,初步解開可論究這些課題的一些線索。
-
-
2007-12-25 出版第43期
-
陳一標 撰 唯識學「行相」(akara)之研究
行相(akara)一詞具有識中所現外境相貌的影像義,以及心、心所的取境作用義。說一切有部認為行相是慧心所中所現的無常、苦、空、無我等相貌。世親在《俱舍論》中則說行相是一切心、心所緣取所緣境的類別,也就是心、心所中所現起的青、黃等相貌。唯識學不承認外境的存在,在心、心所當中安立見、相二分等,以說明認識的構造。相分是所緣,見分是行相,此時,行相是指一切心、心所的了別、領納、取像等取境的作用。 -
無著比丘 原著•蘇錦坤 譯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2)──藉助四阿含解讀巴利經典
-
許明銀 撰 章嘉宗義書(中觀派章)漢譯(二)
-
黃國清 撰 窺基法華思想與唯識學說的交涉
通過《法華玄贊》與唯識相關論書的對照,獲得窺基的《法華經》詮釋於核心義理的層面確以唯識學說為根據的結論。參讀唯識論書對解明窺基的法華思想有莫大助益,甚至可說離開唯識學說的脈絡實難掌握其法華思想的底蘊。
關於佛智的詮釋,窺基將佛真實智分成照真照俗的如體實智與體證真如的證真實智二類,證真實智是一體,內容唯是正體智;如體實照是二用,包括觀無為的根本智與觀有為的後得智。至於實智與權智的關係,後者為方便波羅蜜多,屬後得智,是佛真實智的功用。這種將佛智析分為一體二用的結構,可見於《成唯識論》解說大圓鏡智的內容。
佛知見本應指佛智慧,窺基將其與佛身連結。窺基注釋〈方便品〉的佛知見與〈如來壽量品〉的佛身時用到相同的義理間架,即斷煩惱障成大菩提,斷所知障成大涅槃,而大菩提=報身=佛智(如如智、四智菩提),大涅槃=法身=真如(如如)。開佛知見雙顯涅槃法身與菩提報身;示佛知見顯明三乘平等的涅槃法身;悟佛知見使行者了悟自身本具菩提報身種子;入佛知見勸進實踐一乘菩薩行以成就佛果。
窺基認為〈如來壽量品〉旨在詮說法、報、應三種佛身,他將法身與報身同視為佛的真身,但解說過於簡略。透過唯識相關經論的考察,釐清此處的報身應為佛的自受用身。在大圓鏡智的層次,法身是轉滅阿賴耶識的二障(煩惱障、所知障)所顯,與自受用報身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
釋智學 撰 永明延壽著作綜論
永明延壽(904~975)在中國佛教史上可說是著述頗豐的祖師大德之一。但是,對於他的現存著作群的研究、關心,從早期的《萬善同歸集》、《宗鏡錄》到近年的《觀心玄樞》等,研究的主題也涵蓋了教禪融和、禪淨雙修、《宗鏡錄》中的經典引用狀況,以及泛泛概述其中的某類思想等等。目前所見的諸多成果當然各有其貢獻,然而不免令人覺得奇怪的是,據管見所及,至今為止從事於檢討、論議署名延壽編撰的著作的唯獨僅有冉雲華氏一人而已。另外,日本森江俊孝氏、池田魯参氏、韓國李智冠氏雖然也各自在論文中提出延壽的著作一覧表,但是,其中甚至缺少存佚的檢討,遑論其他。的確,延壽的著作散逸不存者頗多,卷數也頗有份量,所以有其困難度。儘管如此,在延壽的諸多作品重新問世的現今,即使無法面面俱到地進行研究,至少需要重新列舉書目並簡要地檢討。所以筆者將一方面儘可能地過目各著作的原文,另一方面也参考相關研究成果,並兼顧版本、文獻,以提出見解。 -
沈劍英 撰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研究(上)──淨眼論現量與比量
-
-
2007-09-25 出版第42期
-
黃柏棋 撰 初期佛教梵行思想之研究
本文主要由巴利語相關文獻探討佛陀對「梵行」( brahmacariya ) 「梵行者」( brahmacārin ) ,以及其他由「梵」( brahma )字組成之複合詞相涉議題之詮釋。並從對「梵行」等相關複合詞的探討中,進一步歸結出「梵行」字中的「梵 」( brahma )的意義。值得一提的是,佛陀對於梵行等複合詞的重新定義,乃是印度宗教史上重大觀念與時俱進之表現之佐證。而佛教所代表之沙門文化亦對早期印度宗教思想提供了一個新視野。
雖然本文分兩部份來探討梵行與梵行者之意義,不過我們得注意到,梵行與梵行者實是一體之兩面,因此,在佛陀時期,梵行意義之改變也必然牽動梵行者之意涵。就第一部份而言,我們先從如何理解佛陀對於「梵行」這個複合詞所持的觀點談起,最後歸結出,「梵」字在佛陀時期,已從吠陀時期的名詞──指神聖之事等意──轉而被當為一形容詞看待。而其意義包括了清淨 ( pure ) 、卓越 ( excellent ) 、至上 ( supreme ) 、聖潔 ( holy ) 等涵蓋宗教倫理實踐上的新理解。
此一轉變自然關係到佛陀對梵行意義所開創的新氣象。我們見到,梵行之事已被納入佛教宗教倫理實踐之部份,而這不僅呼應著當時的思想氛圍 (intellectual climate),從巴利佛典上來看,即當佛陀創教伊始,它便和「佛教」等同起來,成為包攝修行者整體生活之宗教實踐,而非後來一般所認為的,單單指涉到僧團成員的清淨生活或禁慾狀態而已。
而有關「梵行者」的類似發展部分,我們得將其與其他像婆羅門(brahmāṇa),同梵行者(sabrahmacārin)阿羅漢 (arahant)等類同的詞語放在一起來討論,以便查究梵行者之廣泛意義及同一類屬之措詞,彼此之間的細微差別。這一部份,我們先探討「同梵行者」與「梵行者」之間的不同,以確立像「同梵行者」這樣一個新造複合詞的意義。接著就「究竟梵行」(brahmacariyapariyosāna)來談梵行者與阿羅漢之間的關係。最後再以敘述阿羅漢終極成就之同源套語「無上究竟梵行」(anuttaraṃ brahmacariyapariyosāna)來論述阿羅漢之成就以闡明如何成就最後解脫之道。
必須要強調的是,在佛陀所處的時代、各種宗教思想勃興,有關梵行與梵行者之意涵亦隨之蛻變。也就在這一股重大思想潮流的轉折中,梵行、梵行者及其相關詞的使用,亦表現出了不同以往之意義。終極而言,此一新認同意義與時代的思想氛圍息息相關;而在佛教本身,梵行思想乃為其修行生活賦予了新的宗教意涵,凸顯出其特有的思想風貌。 -
Rupert Gethin著•林明強 譯 見達磨則見諸法:早期佛教“法”之意義考察(因授權問題,不提供線上閱讀)
-
無著比丘 原著•蘇錦坤 譯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1)──藉助四阿含解讀巴利經典
-
陳世賢 撰 世親、眾賢對「三世實有」思想所據「認識條件」的論辯
-
郭朝順 撰 章安灌頂對《大般涅槃經》的詮釋-以《大般涅槃經玄義》為中心
章安灌頂(561-632)為天台智顗最重要之弟子,也是智顗天台三大部之實際整理者,灌頂親撰的作品不多,且如《國清百錄》、《天台大師別傳》等為史傳類的作品,而《觀心論疏》則為注解智顗最後遺教《觀心論》的作品,上述作品都難以直窺灌頂自身的佛學思想,灌頂唯一可能表現其獨自佛學思想的作品,大概便只有《大般涅槃經玄義》與《大般涅槃經疏》二書,因為在智顗生前並未直接講述過《大涅槃經》,然灌頂自稱「管窺智者意義,輒為解釋」 ,因此或許在此「管窺」之中可以掌握到理解灌頂思想的線索。本文集中於對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以下或簡稱《涅槃玄義》)內容的開展,藉此以呈現灌頂對於《大般涅槃經》的詮釋成果。 -
湯銘鈞 撰 對真如的認識與言說──天臺宗、三論宗與慈恩宗二諦論的詮釋
「對真如的認識與言說」是佛教二諦論,即佛教哲學真理論的核心問題。本文將天臺、三論和慈恩三宗有關二諦的論說,作為這個核心問題的解答的三個邏輯階段進行詮釋,以求揭示:對真如的認識與言說的相即(辯證統一)是佛教二諦論的究竟見解。認識與言說的相即就是歸依與教化的相即,歸依與教化的相即正體現了佛教的有所宗尚、不失教化的「即世間而轉世間」的精神特質。這一精神特質值得今日的人間佛教運動記取。
-
-
2007-06-25 出版第41期
-
關則富 撰 從佛教對經驗世界的分析探討念身與四念處的理論基礎及一致性
-
呂凱文 撰 以兩類《大般涅槃經》論兩種佛教典範之判教原則的詮釋學轉向問題
佛教典範轉移運動裡,不少晚後創作的菩薩乘佛典是「援用」與「改寫」自聲聞乘佛典的敘事資源,其中菩薩乘版的《大般涅槃經》是一個明例,它雖然與前輩的聲聞乘版《大般涅槃經》同樣共構於佛陀滅度的故事背景,卻強烈貶抑聲聞乘典範為劣弱,並彰顯出菩薩乘典範的偉大風範,而與聲聞乘版大異其趣。
值得注意的是,在判教原則的抉擇上,聲聞乘版與菩薩乘版《大般涅槃經》存在著差異,各自以「四大教法」和「四依」作為依據。為此,菩薩乘版《大般涅槃經》透過何種詮釋學策略來改寫聲聞乘的「四大教法」為「四依」,以及從「四大教法」到「四依」的判教原則轉向蘊涵著何種詮釋學問題,值得我們細細追問。
在此問題意識上,本文以「對比詮釋」研究方法來分析兩種佛教典範的《大般涅槃經》裡「四大教法」與「四依」的同異處,並分析各自的判教原則的詮釋學特色。本文將說明,從聲聞乘佛教到菩薩乘佛教之間判教原則的詮釋學轉向,帶給佛教典範轉移何種影響。 -
吳汝鈞 撰 佛教空有兩大宗的判釋
-
梶山雄一 著•邱敏捷 譯註 僧肇中觀哲學的形態
-
-
2007-03-25 出版第40期
-
釋智學 撰 中國疑偽佛典研究(一)──永明延壽與疑偽佛典
-
許明銀 撰 章嘉宗義書〈中觀派章〉漢譯(一)
18世紀西藏佛教格魯派學僧章嘉•若貝多傑(lCang skya Rol pa’ i rdo rje,1717-1786),從1736年到1746年,完成他的哲學上的名作宗義書:Grub pa’ i mtha’ i rnam par bzhad pa(略號:CGN)。在他之前,宗義書之集大成,由拉卜楞寺創建者妙音笑金剛(’ Jam dbyangs bzhad pa’ i rdo rje,俗稱嘉木樣一世,1648-1722)的《大宗義》(Grub mtha’chen mo)作為代表作。《大宗義》這本書,其中,第八品有部(24枚,哲蚌•果芒札倉版〈’ Bras spungs sGo mang par〉),第九品經量部(21枚),第十品唯識派(86枚),第十一品中觀自續派(102枚),第十二品中觀應成派(77枚),依此順序論述佛教;而佛教以外的學派,是在第七品以前處理的。一般認為,這是由西藏人完成之理解印度哲學思想之集大成。 章嘉•若貝多傑,即章嘉喇嘛二世是土官三世•羅桑曲吉尼瑪(Thu’ u bkwan/kw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1737-1802)的上師,他的宗義書CGN,即是俗稱的《章嘉宗義書》(lCang skya grub mtha ’)。它是屬於思想史的考察,以深入探討教理的解釋方法而有名。附帶一提,土官三世的有名宗義書為《宗義書水晶鏡》(Gurb mtha’ shel gyi me long,1801)。
前述三位學僧是代表18、19世紀藏區之最高學者,他們是宗喀巴師徒所宣說的印度佛教正統派中觀哲學之代表者。由於目前似乎無漢譯文章介紹,本譯文的第一•二節曾載於《法光學壇》第八期(pp.53-92),2004年。此處重新改訂,另外加上第三節〈中觀派在西藏的歷史〉,一併刊出,其餘部分擬陸續連載,以饗讀者。最後,附上所依藏文版本,及校勘註記,以資參考。 -
屈大成 撰 佛教戒律的方便精神
戒律是僧眾生活和僧團運作的指導原則和依從規範,為佛弟子所必須學習、牢記和遵行。修行法門如三學,以戒為首;八正道中的正語、正業、正命,即為戒律的要求;六波羅蜜之一便是戒波羅蜜。戒律在佛教的重要性,無容置疑。可是,戒律是二千多年前於古印度逐步確立,放諸今天,不少自然難以遵守;但戒律是佛陀所制定,仿如神聖不可侵犯,因而很容易形成衝突和矛盾。十多年前學者已指出,佛教界的現象是「人人受戒、人人破戒」、「不管是出家的或是在家的,都生活在一種雙重人格的、矛盾的……守戒與破戒衝突、聖情與罪惡交戰的複雜心理之下,成了宗教上的分裂性人格」。戒律之要重新檢討,實已逼在眉睫,但又遲遲未行。本文分「初期佛教的戒律觀」和「大乘佛教的戒律觀」兩節,粗略回顧從佛教形成之初到中期大乘佛教的戒律觀,旨在指出戒律的制定偏向特殊性而非普遍性、應用具備方便性而非強制性。今天如仍僵守律典文本,反會窒礙佛教的健康發展。冀本文能對圖改革者提供多少參考材料。 -
佛妙佛學中心2004年圖書目錄
-
-
2006-12-25 出版第39期
-
吳汝鈞 撰 我的判教基準與早期佛教:捨邊中道與法有我無
-
釋智學 撰 石壁傳奧──高僧補敘之一
唐代石壁傳奧(Shibi-Chuanao),是一位生卒年不詳、生平事蹟寥寥無幾的僧侶,據云他是唐代佛學大家圭峰宗密(Guifeng-Zhongmi)(780~841)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曾屢屢為宗密(Zhongmi)的著作再撰注疏,也在《大正藏》(Taisho-pitaka)、《卍續藏》(Manzizoku-pitaka)等大藏經中留下吉光片羽,更在敦煌文獻中留有雪泥鴻爪,也在東鄰的韓國、日本流傳其著作的抄本、刊刻本。然而即使是這樣的人物也難以獲得青睞,既未見載於中國歷代的僧傳,也少見現代學者的矚目。筆者不能漠然坐視,遂乃不揣淺陋,聊敘關於文獻方面的所見所知;至於義理方面,則期諸將來。 -
周慶華 撰 佛教形上語言隱含的難題及其化解途徑
佛教所預設的宇宙萬物的實相以及洞見該實相以便解脫的智慧和解脫後的境界朗現等等,分別以空、般若和涅槃(佛)等形上語言著見,已經成為眾人傳習體證和詮釋著述不輟的對象;但有關該形上語言所指涉的實質究竟如何可能卻還有如煙花閃爍,解說者言詮多為籠統奢華而不實在。這種難題,基本上得回返每一次第的形上語言是經由論者的「限定」而可能的前提上,才能知曉如何的去因應體證一類的課題。換句話說,佛教的形上語言所隱含的「實證」上的困難,在必要化解的情況下得從「人的賦義」中尋隙予以理論兼經驗式的分疏,然後不再預期終極境況而只為它保留「可進」的彈性。從此相關的「紛擾」或可止息,而所有的修行依止的「理據」也才具有正當性。 -
釋長清 著•黃國清 譯 二諦之間的關係
-
德妙佛學中心2003年圖書目錄
-
-
2006-09-25 出版第38期
-
吳汝鈞 撰 《攝大乘論》(Mahayanasajgraha)中的阿賴識(Alaya-vijbana)思想之研究
-
朱冠明 撰 略談《摩訶僧祇律》的語料價值
本文從口語表達和語法兩個方面以舉例的形式說明《摩訶僧祇律》是一部口語化程度較高的文獻,加之其譯者及年代可靠、反映社會生活面廣,因而具有較高的語料價值。 -
辛鶔靜志 著•賀可慶 譯 《長阿含經》原語研究
-
Ven. Bhikkhu Bodhi 原著•蘇錦坤 譯 再訪「井水喻」──探索SN 12.68 Kosambi《拘睒彌經》的詮釋
-
釋長清 著•黃國清 譯 二諦的定義與區分
-
-
2006-06-25 出版第37期
-
沈劍英 撰 淨眼關於因明過失的論議
淨眼在《因明入正理論略抄》中針對文軌的《因明入正理論莊嚴疏》提出不少助解和質難,其中關於因明過失的論議占了一多半的篇幅,並且仍然是有選擇地進行論議,或詳或略,多寡不一。如將論議的重點置於因過,對不成、不定、相違三類似因均有論述,而對宗過和喻過則涉及不多。本文謹就淨眼《略抄》關於過失的論議逐一加以論析。 -
Rupert Gethin原著•林倩 譯 南傳阿毗達磨關於有分心與輪迴再生的學說
-
釋長清 著•黃國清 譯 二諦義理的建立
-
德妙佛學中心2001年圖書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