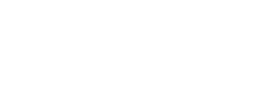正觀雜誌

歡迎來到正觀雜誌社的網頁,我們定期出版的《正觀》,是一本佛教學術研究期刊,懇請十方大德以及專家學者共同支持,也歡迎捐款助印。若您使用本網站撰寫論文或學術研究,請加註說明。歡迎訂閱電子期刊。
| 期刊名稱:正觀 出版者:正觀雜誌社 出版地:南投縣,台灣 出刊頻率:季刊 創刊日期:第1期,1997年6月25日 |
Name: Satyābhisamaya Publisher: JhengGuang Magazine Place of Publication: Nantou hsien, Taiwan Frequency: Quarterly ISSN: 1609-9575 |
正觀雜誌目錄(1-101期)
-
2006-03-25 出版第36期
-
漢斯.康特 撰 從天台宗《法華玄義》「本跡」詮釋方法上探討「指涉」的宗教哲學問題
依德國宗教學家G.. Mensching而言,諸世界宗教都展現為解救學(soteriology)的形式,並且皆具有兩種共同點︰一、解救學對於整個人類拯救之關懷,預設世俗生存之負面義;二、解救學以終極價值為展現,點出生存中之希望因素,也就是其拯救理想的正面義,後者由於不可被侵犯,故是神聖義。人類生存是否可有希望之跡象在於世俗界對神聖義之指涉。可是世俗之負面價值與神聖之正面價值之間存在著一個懸掛狀態,且該懸掛狀態會引發與符號學相關的問題︰既然現實世界體現世俗生存的負面形式,它怎麼還能夠指涉以終極價值為展現人類生存的神聖義?在諸世界宗教不同解救學傳統的脈絡中,世俗與神聖之間的指涉關係該如何被闡釋?換言之,現實世界中「能指」的符號與「所指」的神聖義之間的相對應,應該成為每一解救學脈絡所關注宗教符號學的哲學問題,該問題就屬於宗教哲學領域。
筆者認為,基督天主教的否定神學(negative theology)以及佛教天台宗有關「本跡不二」的探討都會牽涉到該宗教符號學的哲學問題。比如公元500年否定神學家Dionysios Areopagita於De Divinis Nominibus中吸收Proklos(485年)所繼承新柏拉圖學派奠基人Plotin(270年)的符號學觀念,來解釋上帝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重點就在於現實世界當作上帝原型之副本形式,故兩者不相同一而只是相似;在存有上兩個作為不同的層次,兩個之間存在著一個鴻溝,因此否定神學神聖觀在於上帝存在之超越性,世俗與神聖間的關係主要受「人神相隔」的制約。但是由於兩者之間有相似性,世俗界是寫照,上帝則是原形,前者反映出後者;換言之,世界是能指符號而上帝則是所指義。又因為寫照及原形之間的鴻溝,能指與所指非相同一,故所指終究是不可被指明而能指終究是所指的否定形態;Areopagita就說,上帝就像在一切印記當中找不到而能印的圖章原形。該比喻就表示能指與所指之間關係就對應到否定神學神聖對世俗超越性的觀念。
相對而言,佛學天台宗神聖觀順著類似「煩惱即菩提」之說法而強調,世俗與神聖之間具有兩極同體的關係,神聖義呈現為世俗界之逆相引導而世俗界之本質則是神聖的價值引導,能指的世俗界本來就是所指神聖義虛假的倒映形態。該呈現及本質之間具有相依相成一體兩面之構造,故能指世俗之「跡」回溯所指神聖之「本」;與否定神學之不同的是,能指世俗與所指神聖之同體並不代表在存有上兩個不同的領域。智者大師(538-597年)藉以植物的比喻來闡釋能指及所指兩極同體的關係︰「枝葉(=跡)回溯根」與「根(=本)使枝葉根植」,本跡彼此交涉之一體就等於能指與所指相依相成之構造。智者大師在《法華玄義》中繼續指出,只有在使眾生領悟佛法救度學能指之符號本來就具有「跡」身分時,該符號系統才能齊全地展現出其所指究竟義具有與「跡」身分相對而言之「本」身分,並且「本跡」同體之兩極雖互為敵對,但是兩極交互之同體還是作為「本」和「跡」所屬於的整體本身。因此天台宗「本跡」之二分法本來就代表天台宗在對佛法符號系統的反省中所使用的「一體兩門詮釋方法」,且形成《法華玄義》對佛法主要環節「本門十妙」及「跡門十妙」一體兩門的架構。
在不同解救學傳統中就可以針對宗教符號學的哲學問題找到不同的答案。因此專就世俗與神聖之間的指涉關係而言,本研究計劃就列舉以上所提及兩種正好不同解救學的類型,來探討宗教符號學的哲學問題。筆者首先借用對照的方式,去區分西方神祕神學(=否定神學)與東方天台宗佛學兩個解救學傳統針對神聖及世俗之間關係上的不同觀點。將兩種解救學類型之區分展現出來之後,在從兩個不同視野的角度上,筆者就進一步闡釋對於該宗教符號學哲學問題上兩種不同的解決方法。 -
釋長清 著•黃國清 譯 吉藏二諦思想的來源
-
吳汝鈞 撰 宗教義自我的現象學導向與我對佛教的教相判釋(中之一)
-
周慶華 撰 他詮釋了什麼:賴賢宗《佛教詮釋學》討論
晚近的佛學研究普遍傾向「依義解文」的路數,且以跨科為能事,成果也相當可觀。賴賢宗所著《佛教詮釋學》一書,就是以西方哲學詮釋學的理論為骨架,而回返佛教本體詮釋的傳統重新進行體系的創造和當代跨文化溝通潛能的發掘,很可以為佛學研究者參考借鏡。此外,賴賢宗尚未觸及的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諸如佛性存有論如何可能以及佛教認識論和佛教解脫論如何有效的開展等等,則可以留予人對諍的空間,合而展現賴賢宗的著作在當今佛學研究開新上的不凡的意義和價值。
-
-
2005-12-25 出版第35期
-
呂凱文 撰 對比、詮釋與典範轉移(2):以兩種《善生經》探究佛教倫理的詮釋學轉向問
大乘佛教礙於菩薩典範與聲聞典範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思想分歧,因而既不能全盤接受歷史佛陀施設的聲聞律制作為宗教生活的戒學典範,又不能不為新佛教典範設置「新戒學」作為修道基礎,在這「兩難」情況下,該如何從「理想宗教型態期待」來對於傳統聲聞律藏既存的律制加以批判地調整與改寫呢?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至於寫作安排上,首先,本文對於三類大乘戒經進行分析:本文認為大乘戒經的創作與編輯,與當時印度歷史現場裡,大乘思想家必須面對的三種宣教對象密切相關;為了融攝外道、在家居士與出家聲聞佛教徒,三類大乘戒經的論述模式與思想內涵,也就分別共構在印度神教、在家與出家聲聞佛教的敘事資源上,且無法從中割離出來。其次,本文將焦點置於在家居士佛教倫理的典範轉移問題:藉由兩種佛教典範《善生經》的對比,仔細說明大乘佛教如何「擴大改寫」《善生經》為《優婆塞戒經》,並促成佛教典範轉移與導致佛教倫理的詮釋學轉向。最後,則是本文的結論與展望 -
邱敏捷 撰 佛教《六方禮經》之倫理觀探析
《六方禮經》乃佛教倫理學的重要經典之一,其內容係就親子、師生、夫婦、親友、主從、僧俗等「六方」人際相互對待之「應然」關係,提出行為準則。在「親子倫理」上,該經規範「子對父」有奉養所需、豐足生活與益其心志之責任;「父對子」則有愛護照顧、教育成人、完就婚嫁的義務。在「師生關係」上,要求「生對師」務尊禮懷恩、敬送束修、敏於受教;而「師對生」則要勤於授業、擅解疑惑、善教勝師。在「夫婦關係」上,期許「夫對妻」應愛敬有加、委付家內、自律專情;而「妻對夫」則要敬順善待、貞淑守德。在「親友關係」上,希冀親友之間互敬相濟、勸善規過。在「主僕關係」上,規範「主對僕」須照顧無遺、適才適用、制度合宜、利益共享;「僕對主」有嚴守職分、細心奉迎之德。在「僧俗關係」上,明列「俗對僧」宜誠心尊禮、敬施供養;至於「僧對俗」則有教誨善法、身教度世之本分。可以說,《六方禮經》具有(一)適應世俗社會的生活需要,(二)強調平等互敬的對待關係,(三)重視文化傳承的學術意涵等三項特質。 -
郭忠生 撰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九)
-
-
2005-09-25 出版第34期
-
呂凱文 撰 對比、詮釋與典範轉移(1):兩種佛教典範下的郁伽長者
儘管初期佛教的開展以人類歷史的釋迦牟尼為中心,但是聲聞弟子集結的三藏聖典暨聲聞典範阿羅漢,與後起的大乘佛教的三藏聖典暨菩薩典範卻存在相當程度差異。鑑於前後兩種傳統的三藏聖典暨宗教典範存在著不可共量性,因而在當代學術研究意義的歷史學嚴格觀點下,後起的大乘佛教起源等問題頗受爭議。其中,部份學者指出,大乘佛教的興起與部派佛教的出家僧伽沒有直接關係,反而與在家佛教徒的宗教解釋運動相關。儘管學界對該類論點褒貶不一,但是它也提示一種解讀與觀看大乘佛教起源的重要觀點,亦即從在家佛教徒的角度理解。
順此理解角度的啟發,本文擬以「對比」模式,透過詮釋學觀點與意趣,烘托初期佛教與大乘佛教兩種佛教典範的聖典,如何透過同一位在家佛教徒,建構各自宗教傳統的特定人格生命典範。本文藉此人物出場的語境脈絡之對比,突顯兩種佛教典範之敘事內容的同一性與差異性,進而析論前後兩種佛教典範轉移之際的變遷軌跡,審視大乘佛教起源說的詮釋學問題。此外,本文對於前後兩種佛教典範轉移所涉及的「詮釋衝突」問題,亦嘗試另闢「新徑」重新審思與解讀。 -
釋長清 撰 吉藏《金剛般若疏》之初探
身為三論宗的結集者-吉藏,深受般若的洗禮;又其對空之詮釋,具有特殊的看法。因此,對于吉藏《金剛經》的解釋很值得我們去注意及探討。
筆者只是嘗試對其作品-《金剛般若疏》,作一個初步的探討。筆者發現吉藏主要是依據其老師-法朗,以「無得」、「不住」、「無所著」為中心教義。因此,吉藏是以「無得正觀」為其主要理論根據來詮釋《金剛經》。其實,這也是吉藏以「無得正觀」為基本精神教學。除此之外,吉藏也以其所暢談之重要理論如方便、中道、教理、因果、體用等來解釋此作品。的確,我們發現吉藏對般若有其獨到的見解及風格。因此,我們對于《金剛經》的詮釋更有另一種選擇及看法。 -
蔡耀明 撰 文獻學方法及其在佛教研究的若干成果與反思
-
-
2005-06-25 出版第33期
-
溫宗堃 撰 巴利註釋文獻裡的乾觀者
本文探討巴利註釋文獻裡,關於「乾觀者」的三個問題:(1)乾觀者的定義;(2)其修行方法;(3)三藏聖典中,哪些資料被註釋文獻視為與乾觀者有關。研究發現,(1)即使得似相、近行定,禪修者若未得禪那,便修習內觀,即名為乾觀者。(2)乾觀者初修內觀時,多偏重觀察色法,即從「四界分別」著手。相對於得禪那者,乾觀者未具禪那成就,若初修內觀感到疲累時,沒有現法樂住的禪那可作休息處;再者,乾觀者能夠觀察的所緣,也只限於欲界的名、色法。(3)《尼柯耶》有不少的經文被註釋文獻認為是在描述「乾觀者」,然而有被明確揭示其名字的「乾觀者」,似乎只有兩位而已。 -
吳汝鈞 撰 宗義自我的現象學導向與我佛教的教相判釋例(上)
本文的部分內容,抽自正在撰寫的拙著《純粹力動現象學》。在這篇論文中,我要通過對具有宗教義的自我的探討,作為線索,引出我對佛教的判釋或教相判釋。在對自我的判準方面,我提出軀體我、靈台明覺我、同情共感我、本質明覺我、委身他力我、迷覺背反我與總別觀照我。其中,軀體我的層次太低,總別觀照我是認知義,它所成就的知識基本上是方便、權宜的性格,不具有濃厚的價值的、理想的現象學意義,故都不是現象學導向的自我。在餘下的五種自我,則具有現象學意義,但靈台明覺我與同情共感我分別相應於藝術觀照我與德性我,沒有濃厚的宗教涵義。餘下的本質明覺我、委身他力我與迷覺背反我則純是宗教性質而又具現象學意義或導向的自我。因此我要在這裏集中探討這三種自我,並看它們如何關連到我對佛教的教相判釋,讓我得到啟示與比較意義的助益。 -
許明銀 撰 佛教徒宗教交流.對話管見
-
德妙佛學中心2000年圖書目錄
-
-
2005-03-25 出版第32期
-
廖本聖 撰 至尊.法幢吉祥賢著《宗義建立》之譯注研究
印度佛教主要分為四大宗派:屬於小乘的毘婆沙宗、經部宗,以及屬於大乘的唯識宗、中觀宗。其中,每一宗均有它獨特、不共的修行理論,這些修行理論被稱為「宗義」或「學說綱要」;而闡明這些修行理論的著作,就名為「宗義書」或「學說綱要書」。
依據佛教的宗義,若不了解「無我」的道理,是不可能徹底斷除煩惱及痛苦的根本--我執--及其習氣而解脫、成佛;因此,佛教各宗的宗義書,就是從自宗的角度去說明無我的見解。一般均認為:中觀宗的無我(=無自性=空性=無實有)見解最究竟;而了解下部宗義,則是通往上部宗義的階梯。
在西藏格魯派當中,題名為「宗義建立」的著作不只一部,本文所要處理的是至尊.法幢吉祥賢所著的《宗義建立》,而這部論也是格魯派三大寺當中的色拉寺伽僧院及甘丹寺北頂僧院這二個僧院所共同使用的教科書,因此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
陳世賢 撰 《成實論》「三心」與《攝大乘論》「三性」思想之比較
-
關則富 撰 Saññā and Sati想與念
正觀第17期刊登拙作「初期佛教之四念處」。該文指出四念處中的身、受、心相當於五蘊中的色、受、識,並主張四念處未涉及想蘊是因解脫者無想。關於解脫者無想這一論點,當時已提到學者有不同的意見。本文旨在修正此論點,提出一個不同的見解,大意如下: 經文中所說解脫者應捨離的想並非泛指一切的想,而是指不善巧的想。例如《經集》中的《八篇章》與《中部》的《蜜丸喻經》所破斥的想是指會導致戲論(papañca)的想。本文並探討想與念(sati,或譯「正念」)在認知功能上的多項共通點,依《蜜丸喻經》等經典所述的認知過程,闡明念的作用即在於導正想蘊,以成就善巧的想。承蒙正觀雜誌惠予進一步探討的機會,特此致謝。由於前一篇文章以英文刊登,為顧及前文讀者中有不懂中文者,故本文仍以英文發表,造成許多讀者的不便,尚請見諒。本文之大部分節錄自筆者的博士論文。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earlier in this journal (vol. 17), I argued that the first three objects of the four satipa hānas correspond to rūpa, vedanā and viññāöa among the five khandhas, but saññā is not involved in the four satipa hānas because a liberated person has no saññā. While quoting two canonical passages to support that a liberated person is devoid of saññā, I also indicated that Sue Hamilton (1996: 60) had disagreed with me and contended that “saññā not only apperceives and conceives all our saµsāric experiences, sensory and abstract, but is also instrumental in identifying the liberating experience” on account of a canonical passage which describes the experience of liberation as being the highest activity of saññā. After more investigations, I have found that my argument that a liberated person has no saññā was wrong. Here I would like to show that those passages that criticise saññā and dissociate it from liberation only disapprove of unwholesome types of saññā, and that the practice of sati consists in the wholesome functioning of saññā. Let us first examine what saññā and sati refer to.
-
-
2004-12-25 出版第31期
-
何建興 撰 法上《正理滴論廣釋.現量品》譯註
-
沈劍英 撰 淨眼論因明之能立
-
吳汝鈞 撰 我與梶山雄一教授:一點關係與哀思
-
越建東 撰 早期佛典禪修公式在不同文本中所呈現之特質
本文旨在探討佛教之禪修公式在早期佛典中(以漢譯阿含經和巴利尼柯耶為主)的呈現情形。文中選取了兩個公式作為討論的例子。這兩者皆取自於早期佛教中可能是最長、最核心的一個修行道架構。此道架構又可以用巴利《沙門果經》(DN2)所記載者為代表。
第一個要說明的公式為「初禪公式」,第二個用來舉例者則為「根門守護公式」。在「初禪公式」中我們發現DN2之描述,特別是在公式之前序句(introductory sentence)部份,與其他版本有一些出入。在比對的過程中我們採用了多元化的對象,包括應用漢、巴、梵語版本的《沙門果經》或相當經,以及其他與《沙門果經》無關但也是在描寫同樣道架構的阿含經類。
在比對中,我們著重平等看待各版本之間的差異和相同點,從分析這些異同點中我們提出幾點值得探討之處:為何DN2有其獨特的表達方式?其原因何在?這種異於它者的方式有甚麼根據和用意?為何各版本之間會產生異同?在排除了版本斠勘學的原因之後這些異同點的特徵顯現了某些更深刻的意義。其中譬如對禪修公式的傳播和使用,乃至對早期佛典的集成與傳播的理解具有某些提示。弄清這些特質,對我們回顧和了解佛典之傳誦(如口傳文獻、傳誦師、教義公式化、佛典編制體例原則等等課題)也許會有不小的幫助。這些意義在本文的第二個例子中也有所補充和說明。
透過以上兩個例子,我們可以找出一些禪修公式呈現方式的特質。筆者認為,若我們能夠以類似的方法去檢驗更多禪修公式的話,我們可以發現、累積到更多不同的特質,進而歸納出公式中一些重要的體例。本文結論所嘗試要表達的是:徹底的、多重的比對是必要和有用的。經過深度比對的結果,我們即可利用某些發現來檢討目前學界對佛典傳承史所提出的模式或假說。
-
-
2004-09-25 出版第30期
-
郭忠生 撰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八)
-
吳汝鈞 撰 與京都哲學的對話:西谷啟治論宗教、道德問題與我的回應(下)
-
許明銀 撰 西藏佛教研究的意義
-
Lance Cousins 原著•溫宗堃 譯 內觀修行的起源
-
-
2004-06-25 出版第29期
-
郭忠生 撰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七)
-
吳汝鈞 撰 與京都哲學的對話:西谷啟治論宗教、道德問題與我的回應(上)
-
黃文樹 撰 王門弟子與佛教
王門弟子繼承陽明的學風,同佛門人物密切交遊,究心佛乘禪趣,深受啟迪。所謂「含其英,咀其華,自然得他好處。」他們吸收佛教「人皆有佛性」及「自性清淨」理論,衍生「復明 本心」的人生修養觀;效法僧眾「佛化農工」的精神,實踐化及平民的社會教育事業;認同佛教義理,採取佛旨禪趣作為主要的講學內容之一;採納佛教「直指人心」的教法,建立「自證自悟」的教學原則;融入佛教禪修及心印的模式,應用「禪定心授」的教學方式。
-
-
2004-03-25 出版第28期
-
越建東 撰 馬鳴在《美難陀》中對「瑜珈」(yoga)及其相關詞的用例
-
郭忠生 撰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六)
-
廖本聖 撰 西藏心類學簡介及譯注
-
德妙佛學中心1999年圖書目錄
-
-
2003-12-25 出版第27期
-
漢斯.康特、郭朝順、米建國 合著 引言:東西哲學對話:語言的界限
-
漢斯.康特 分論:天台宗的可說與不可說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usage of language and soteriological conception in Tiantai Buddhism.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is issue is the question of the limits of verbal expression raised by speculative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in this Buddhist school. According to the Tiantai Buddhist vision of soteriology, the limit between the expressible and the inexpressible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turning point from intentional usage of language into its pragmatic mode.
Intentional usage of language includes that kind of verbal articulation, which expresses cognitional and volitional contents of consciousness. Pragmatic usage of language refers to verbal articulation, which functions as means of expediency within a soteriological context. Tiantai Buddhism regards verbal meanings construed by intentional usage of language as ultimately unreal, and all entities identified with these meanings are considered as illusory. Existing things are believed to be devoid of any substantial reality of itself; but recognized as discrete entities corresponding to verbal meanings, their original non-abidingness is inverted into an abiding substance, which is regarded as illusory. However, this illusory state of inversion caused through intentional usage of language includes an instructional value, because it inversely refers back to what is real. The pragmatic relevance of this instructional value is signified, then, as provisional mode in verbal articulation. Pragmatic usage of language emphasizes the provisional character of verbal meaning by means of paradoxical articulation. As soon as some soteriological meaning is verbalized, it must be denied, to signify its provisional character. Pragmatic usage of language maintains its reference to the soteriological meaning of “non-attachment” by means of paradoxical articulation. It constructs and simultaneously restricts meanings to its provisional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ve function of paradoxical articulation. Intentional usage turns then into pragmatic usage of language, and the latter is supposed to be capable of embodying the Buddha-dharma’s ultimate meaning. Consequent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modes of using language consists of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ttitudes of “attachment” and “non-attachment” to verbal meanings.
In Tiantai Buddhism the verbalized represents the illusive realm; the inexpressible represents ultimate reality. On the other hand, ultimate reality cannot but be manifested through this inverse mode of illusory meaning in verbal articulation; and the illusory realm cannot but be based on ultimate reality. As soon as one of the two i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other cannot be neglected either. If the inexpressible were completely devoid of any reference to linguistic articulation, it would be finally meaningless, which entails nihilism; even its soteriological meaning would be baseless. Conversely, the verbalized inversely hints at what is ultimately real – the inexpressible. Essentially, the verbalized is then the inexpressible in its mode of illusive inversion. Tiantai Buddhist soteriology claims paradoxical identity of ultimate reality and its mode of illusion. Ultimate reality devoid of its inversion into illusion would be nothingness. Its inversion into illusion is a necessary device of manifesting its soteriological value. Soteriology of Tiantai Buddhism essentially relies on the viewpoint that the sacred and profane exclusively refer to each other. The illusory moment of the profane manifes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acred by means of “instructional inversion.” Consequently, the soteriological doctrine of “non-duality between the sacred and profane”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issue of the expressible and inexpressible in Tiantai Buddhism. Tiantai Buddhism expresses its dialectics between the verbalized and inexpressible corresponding to the “non-duality between the sacred and profane” through the doctrine of “threefold truth”. In this paper I will display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inexpressible and verbalized according to the Tiantai viewpoint of “threefold truth”.
本文旨在,分析出與天台宗之救度學義相關的語言用法,以及天台宗對語言界限上的觀點。天台宗將「度一切眾生」視為其救度學理想;就其理論性的根據而言,天台宗不得不預設「聖凡不二」之教義。智顗認為,基於此一教義才能顯示出,天台宗「轉識成智」的教化方式所以完整「度一切眾生」的理想。但是依大乘佛教而觀,佛法之聖賢義為不可說,所以一切文字表達只能代表一種世俗義。
筆者認為,依天台宗而言,世俗義之「可說」與聖賢義之「不可說」兩個領域之間的界線可以被理解為「意向性的語言用法」與「實用性的語言用法」之間的轉變點。意向性的語言用法指是,語言表達在一切意識活動的認識以及意志趨向上所指涉的名義;實用性的語言用法則指的是,語言表達在佛法救度的功夫上的手段義。天台宗認為前者所成立者為虛假,但是它含有其價值引導;在其暫時性的形態中,意向性的語言用法發揮文字表達的實用涵義。後者依其暫時性之實用涵義來展現佛法之終極意義。因此兩種語言用法之差別在于一種「執著」及「無執著」之不同。「可說」之詞義關涉到一種既虛假也限定的對象界,「不可說」體現為一種多重涵義的終極實在本身;然而終極實在不得不倒映於與其相反的虛假形態而呈現,而虛假的領域仍須依于一終極實在的根源;是故舉其一端必具另外一端,是故「可說」與「不可說」之間,乃是實在與虛假之「敵對相即」或「同體不異」。
因為如此,天台宗並不將「可說」與「不可說」構思為兩種彼此排斥的領域;依天台宗的辯證法而言,世俗性之「可說」與聖賢義之「不可說」雖互為對立,其卻交互指涉。因此其交互指涉亦對應到天台宗「聖凡不二」的救度依據。天台宗借用「三諦」的中國佛學術語來展現其語言哲學義。本文專就與天台宗「三諦」觀相關聯的語言哲學義加以探討。 -
郭朝順 分論:華嚴宗的可說與不可說
華嚴宗判佛教為小始終頓圓五教,三祖法藏(643-712)將頓教說為離言真如,頓教乃作為由可說之小始終教跨向圓教之時,所特別標舉出之不可說的特性。然其可說與不可說之關係略分可分為兩重︰一是頓教之可說與不可說﹔一為圓教之可說與不可說。頓教與圓教對此問題有不同的說法,但皆主張可說與不可說是不一不二,亦即可說與不可說彼此是圓融無礙。
若依同時也是禪宗荷澤系法裔之華嚴四祖澄觀(738-839)五祖宗密(780-841),則認為頓教等同禪宗,華嚴思想與禪宗之關連性,日人鎌田茂雄編有《禪典籍內華嚴資料集成》(1984東京:大藏出版社)一書已可資證明,禪宗倡教外別傳直指心性,參究公案遂為開悟之重要方法,然禪宗公案之「可說與不可說」推其原始,應與華嚴頓教有其相關。
華嚴與天台思想代表中印佛學融合後的兩種不同的型態,但共同以「圓教」為最終極的教法,其中有差異也有相同之處。歷來天台與華嚴之間即不斷相互吸收、相互批判,其對話傳統已逾千年。然二者就其作為教導眾生證悟絕對真實的法門此一本質來說,其必然面對可說之教法與不可說真實之間的弔詭,因此對語言限度的思考,便為其哲學理論建構的必要課題,而再加入維根斯坦對語言界限的反省,形成天台華嚴與維根斯坦三者之間的多重對話,對於華嚴宗哲學之研究可以開發一種全新的方向,也可以令人重新思考天台與華嚴哲學的差別。
Huayen Buddhism classifies Buddhist doctrines according to five types of teaching: the small teaching, the initial teaching, the final teaching, the sudden teaching and the perfect teaching. The third patriarch Fazang(643-712) explains the sudden teaching as true suchness beyond words. The sudden teaching is marked by the inexpressible; it combines the small, initial and final teaching with perfect teaching. However, the interrelation of the expressible and inexpressible can be distinguished in two ways: the sudden teaching type and perfect teaching type. Both of them rega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ble and inexpressible as ‘non-identity and non-duality’, it means that expressible and inexpressible can not obstruct each other, but cohere with each other.
The fourth and fifth Huayen patriarchs who simultaneously were Chan disciples held that the sudden teaching is nothing but Chan-school. The Japanese scholar Kamadashigeo pro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yen and Chan Buddhism in his work The Collection of Huayen-materials in the Chan-canon (Tokyo 1984 Taishou). The Chan-school promulgated the idea of transmission beyond teaching directly from mind to mind. It employed the methods of Gongan to initiate enlightenment. Originally the expressible and inexpressible of the Gongan in Chan-school is related with the sudden teaching in Huayan-school.
Huayen and Tiantai Buddhism represent two type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heir ultimate level of teaching is identically called ‘perfect teaching’, but except this commonality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Historically, there was a lot of mutual influence, exchange and critics between these two schools, in total their dialogue has been lasting for more than thousand years. Both of them must face the paradox of the expressible teaching-level and inexpressible truth, when they instruct sentient beings to experience ultimate truth. For that reason, their thoughts about limits of language become a necessary concern of their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speculations. If Wittgenstein’s standpoint about limits of language is taken into account, a complex dialogue between the three standpoints of Tiantai, Huayen and Wittgenstein can be developed and possibly a new tendency in Huayen studies might be explored, which might also be fruitful for shedding light on differences between Huayen and Tiantai. -
米建國 合著 分論:維根斯坦論可說與不可說
在當代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中,維根斯坦是一個主要的代表人物,本文主要針對他(早期的著作中)的語言哲學觀點,特別是他對語言界限的看法進行研究。而作為一個整合型的研究(東西哲學的對話:語言的界限),本文也試圖為「可說與不可說」的問題積極地尋求解答。
本文一開始要先回答為什麼討論「可說與不可說」這個問題有其必要性,並試圖論證如果維根斯坦所做的一切是屬於哲學工作的話,那麼對他來說,解釋什麼是可說的以及什麼是不可說但卻可被顯示的,將是哲學工作中的核心問題。
進一步,我將建構維根斯坦哲學中為「世界、思想、和語言」之間所設立的三重連結組織〈而非一般所謂的「世界與語言」之間的二重連結而已〉,並尋求它們之間的共同結構;我將解釋為什麼「邏輯實在論」會是維根斯坦所能接受的必然結果,而「可能世界」這個觀念將是理解「邏輯實在論」的重要切入點。也就是這個存有學的主張,我們才能說明世界中的原子事實、思想中的邏輯圖像、與語言中的基本語句之間的共同邏輯形式。
建基於邏輯形式之上,我們便能為「可說與不可說」之間的區別〈同時也能為「可想與不可想」之間的區別〉立下一個判準,這個判準十分類似於後來邏輯實證論者所主張之經驗意義的可檢證原則,或者我們可以說可檢證原則其實源自於維根斯坦的「可說與不可說之判準」。
最後,我還要澄清並非一切不可說者皆可被顯示,只有一些有限範圍內的不可說者才能被顯示,例如語言的界限、語言的形式或邏輯特徵、事實和語句間的共同邏輯形式、實在界的邏輯形式、事物的存在、以及世界的存在等。我還要強調所謂不可說但可被顯示者必須在可說之中被顯示(其中邏輯恆真句是一部份特殊的例子,因為雖然他們是可說的,但卻沒說什麼)。而對於不可說也不可顯示者,我們必須保持沉默。 -
漢斯.康特、郭朝順、米建國 合著 對談:東西哲學對話
-
-
2003-09-25 出版第26期
-
溫宗堃 撰 漢譯《阿含經》與阿毗達磨論書中的「慧解脫」
近來南傳佛教尤其是其內觀禪法逐漸在台灣興盛起來。這些當代禪法之中,有一些是基於南傳上座部裡所謂「純觀行」或無禪那「慧解脫」的教理而發展出的內觀禪法。本篇論文的目的在於探討北傳漢譯的《阿含經》與阿毘達磨論藏之中是否也存在所謂無禪那「慧解脫」的修行理論。研究結果顯示:說一切有部所傳的漢譯《阿含經》確實描述:在佛陀時代就已存在慧解脫阿羅漢,他們未證八解脱但得漏盡。特別是《雜阿含》〈須深經〉談到一類未得禪那但得解脫的阿羅漢。有部的《大毘婆沙論》與《成實論》也都明確提到此類無禪那阿羅漢的存在。其中,《大毘婆沙論》更將之名為「全分慧解脫」。全分慧解脫阿羅漢所依止的定力,在有部《發智論》與《順正理論》被清楚地界定為「未至定」;在《成實論》中,則是被說為「電光定」。這樣的結果若進一步併合南傳上座部的說法,可以得知:慧解脫的修行傳統並非南傳上座部所獨創的後期產物,而是大多上座系(Skt. Sthavira)部派所共有的教義。 -
郭忠生 撰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五)
-
吳汝鈞 撰 日本京都哲學與佛學之旅與三木清的構想力邏輯
-
邱敏捷 撰 僧肇與老莊思想
-
-
2003-06-25 出版第25期
-
釋若學 撰 「式叉摩那」考
-
郭忠生 撰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四)
-
徐文明 撰 僧叡慧叡非一人辯
僧叡與慧叡同為東晉時期的高僧,又都是鳩摩羅什的弟子,因此多有誤將二者視為一人者,本文批駁了日本學者鐮田茂雄等人的觀點,認為二者不可能是一人。 -
周慶華 撰 後佛教倫理學
-
蔡耀明 撰 佛教研究的進展程序在操作步驟的釐定
在研究所階段從事佛教研究的工作,研究方法的講究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就此而論,廣義的研究方法至少有五大要項,值得多加鑽研:首先,建立學術上治學的基本觀念、研究論文構思的指導原則,以及生起學術論述在格局大小與階次高低的衡量眼光; 其次,對於當代佛教研究致力於走上專門的學術探討、穿戴學術的包裝,從而在方法和內容的運作形態、可能的弊端、以及若干可行的改善之道,都培養出最起碼的認識和省思; 第三,佛教研究在研究進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之間的區分,以及培養多元的研究進路觀; 第四,形成具體可循的研究步驟,以及研擬研究計畫或論文大綱; 第五,針對個別的研究進路,例如語言文獻學的進路,就該進路所對應的研究工具、操作技術、講究手法、預設理念、獨特眼光、具體範例、以及夠份量的學術論著,逐一進行專門的練習和思辨,如此才足以在個別的研究進路深入堂奧,並且練出可站到學術第一線從事開拓性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