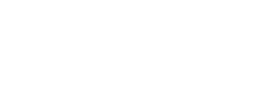歡迎來到正觀雜誌社的網頁,我們定期出版的《正觀》,是一本佛教學術研究期刊,懇請十方大德以及專家學者共同支持,也歡迎捐款助印。若您使用本網站撰寫論文或學術研究,請加註說明。歡迎訂閱電子期刊。
| 期刊名稱:正觀 出版者:正觀雜誌社 出版地:南投縣,台灣 出刊頻率:季刊 創刊日期:第1期,1997年6月25日 |
Name: Satyābhisamaya Publisher: JhengGuang Magazine Place of Publication: Nantou hsien, Taiwan Frequency: Quarterly ISSN: 1609-9575 |
正觀雜誌目錄(1-101期)
-
2021-06-25 出版第97期
-
陳一標 從真理的「如實性」與「無顚倒性」看瑜伽行派三種勝義成立的脈絡與內涵
一般認為世俗諦是世間的真理,勝義諦則是出世間的真理,從被認識的客觀面來掌握它們。但是《辯中邊論.真實品》在解釋勝義諦時,曾巧妙地運用梵文解釋複合詞的依主釋(tatpuruṣa)、有財釋(bahuvrīhi)、持業釋(karmadhāraya),將其拆解成「最殊勝的無分別智的對象」、「以最殊勝者為對象或目的的」、「最殊勝者就是義利(利益)」,而且分別具體指涉真如、勝道、涅槃,而這三者正好就是修行所應悟的境、所應修的行以及所應證的果。而中觀學派的清辯同樣依三種複合詞解法所得到的是「最殊勝的無分別智的對象=真如」、「隨順勝義者=般若」、「最殊勝的對象=真如」,其中隨順勝義與勝道的內含相通,涅槃不外是真如的實證,所以唯識與中觀所說的三種勝義的解釋是相近的。
本文嘗試從佛教當中與真理相關的概念來做分析,企圖由此找出唯識學派三種勝義成立的脈絡,並由此深入理解其內在意涵。結果發現「法」這個概念,若站在佛教重視實踐的精神來看,其最首出的意義在於作為八正道的「中道法」,但也可含攝所觀察的緣起、四諦的真理以及所證得的解脫境界亦即涅槃。《俱舍論》在解釋阿毘達磨時說無漏慧因為可以對觀四諦、對向涅槃,所以是勝義的阿毘達磨,也可看到以慧行對理境與行果的架構。再看唯識學派在解釋「諦」時,除了強調其「如如(tatham)、不離如(avitatham)、不異如(ananyatham)」的「如實性」(bhūtatā)外,還強調其自相不會欺瞞,見其自相會有不顛倒的覺知(buddhi)或勝解(adhimokṣa)現起,也就是諦還有「無顛倒性」的一面,前者被稱為所知真如,後者被稱為能知真如。
透過對唯識學派有關「真實義」(tattva-artha)(含二種真實、四種真實、六種真實)與二諦、三性、五法(相、名、分別、真如、正智)之對應關係的研究,發現唯識學最終將世俗定義為「有漏的心、心所以及它們所認識的對象」,將勝義定義為「無漏的心、心所以及它們所認識的對象」,乃是承繼著佛教以實踐為核心關懷,談真理必然與去除了染污、障礙的主觀的智慧不相離的,甚至於說智慧即是真理。於是在解釋勝義的語義時,一方面巧妙地符合梵文複合詞的解釋方法,一方面在教義上,使勝義同時具有真如、勝道、涅槃的意涵,承載著修行的境、行、果的角色。
-
蘇錦坤 《大正藏》頁底註的訛誤─以第一、二冊為主
《大正藏》在「全新的組織架構」、「收錄豐富的古譯、漢地著述與日人著述」、「精審的校勘」、「嚴謹的校勘目錄」、「收錄敦煌文獻」、「收錄早期教外譯典」、「收錄歷代疑偽經典」以及「完整的經號編序」等等,都立下「雕版大藏經」的典範。
雖然如此,《大正藏》也有不少瑕疵;如印順法師提到:「有些經是重複而應該刪削的;有些是編入部類不適當的;有些是同本異譯,分編在各處,沒有注明而不便初學的」。」
方廣錩在《佛教文獻研究十講》一書也提及《大正藏》亟待修訂的訛誤,例如:「以《頻伽藏》為『工作稿』,卻誤將前者的錄文混入《大正藏》正文當中」。
本文接續兩位先進的文脈,對於《大正藏》第一、二兩冊的頁底註,依次列舉「巴利對應經文」、「對應經典」與「校勘瑕疵」三類訛誤。《大正藏》引述「巴利對應經文」時,有「經名不正確」、「拼寫訛誤」與「引文訛誤」等三種現象。所列的漢巴「對應經典」,因當時尚屬「漢巴經典對應目錄」的草創時期,失誤在所不免,所以學子應避免參考此類資料。本文所列「校勘瑕疵」,主要是論列與《大正藏》「校勘體例」不符的例子
當然,本文目的不是為了批評、指摘《大正藏》的短處,而是提供一些意見,作為將來修訂《大正藏》或編修「新藏經」的參考,也藉以提醒初學者引述《大正藏》經文及其頁底註時所需警覺之處。
-
楊惠南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171首~第200首
日治時期的古典佛詩,由於台灣已經淪為異國殖民地,再加上由日本間接輸入的西方民主開放的思潮,以及「祖國」(清國)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等等的隔岸呼喚下,台灣佛詩又恢復了詠史的特色,同時也含有「逃禪」的意味。但這一階段的「逃禪」性格,與第一階段的明清時期不同。這一階段的「逃禪」詩,作者本身少有「逃禪」者;而是對明鄭時期「逃禪」者,例如對沈光文、李茂春等人的悲憐。
-
-
2021-03-25 出版第96期
-
呂凱文 從佛教觀點看神經語言程式學
這篇文章可以視為是一種嘗試的比較,亦即嘗試從廣義下新時代運動所引發的身心靈技術當中,選擇其中一項,並藉此從另一種傳統宗教既有的身心靈技術重點地考察。考慮的幾種選項中,選擇新時代運動裡被視為嚮導之一的「神經語言程式學」(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以下略稱為NLP)作為對比項,至於傳統宗教裡的佛教(原始佛教)則是另一個對比項。這種對比的意義,不僅可以從對比中看出舊典範的資源以及新典範的創意技法,也可以藉此促成處於當代處境的舊典範如何翻新身心靈技術的思考。
-
蘇南望傑 藏譯佛典譯語初探--以藏文《心經》為中心
近年來學界研究注意到藏譯佛典中近代的文本存在不少「修正」的痕跡,通過比對研究也發現,較為古老的藏譯佛典寫本往往與梵文或原文較為一致。因此也對於廣泛流通的木刻本「存疑」,同時對所謂「東部系統」的蔡巴與「西部系統」的廷邦瑪,兩大《甘珠爾》主要系統之歷史文本開始受到學界的重視,另外隨著愈來愈多的諸如普札(Phug brag)、塔波(Ta pho)、巴塘(’Ba’ thang)等所謂「孤本(Proto)」之發現,使得相關研究成果也陸續出現。
再者敦煌藏文文獻應視為目前現存最早的藏譯佛典文獻之一,時間可追溯到8至9世紀,內容包括小乘、顯密等所有經論,其數量相當可觀。這些文獻對於想要了解藏譯佛典最早的譯經歷史;認識吐蕃王朝贊普時代「文字釐訂」及「欽定譯語」時期佛典翻譯用語所發生的前後變化;《聲明要領二卷》、《翻譯名義大集》等官方所訂定的譯語彙整資料等,相信這對於了解最初的藏譯佛典原貌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依據上述譯經歷史及文獻,以近代流通最廣的《德格版》「藏文《心經》」為主軸,嘗試以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如P.T.447、P.T.449、P.T.457;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如IOL.Tib.J.VOL.31、IOL.Tib.J.VOL.32等幾篇寫本,並結合原先屬於東、西部系統版本的寫本及近代大量流通的那塘、北京、拉薩等木刻本作為相互比較資料,以「藏文《心經》」為中心,試圖探討藏譯佛典新、舊譯語之演化、版本間的差異性、語順、詞性的改變、簡化構成字母及後期版本所出現的「修正」痕跡。六
近年來佛典傳譯計畫盛行,譯者個人或團隊將某一經典新譯為其他語言之前,應先對該經典的翻譯史,不同文本,以及文本間的差異性,文本校勘、考證等,進行謹慎仔細的文獻學研究,使經典傳譯事業更經得起檢驗,這也是本稿研究之意義所在。
-
楊惠南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 日治時期第151首〜第170首
日治時期的古典佛詩,由於台灣已經淪為異國殖民地,再加上由日本間接輸入的西方民主開放的思潮,以及「祖國」(清國)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等等的隔岸呼喚下,台灣佛詩又恢復了詠史的特色,同時也含有「逃禪」的意味。但這一階段的「逃禪」性格,與第一階段的明清時期不同。這一階段的「逃禪」詩,作者本身少有「逃禪」者;而是對明鄭時期「逃禪」者,例如對沈光文、李茂春等人的悲憐。
-
-
2020-12-25 出版第95期
-
釋知如、釋慧法、林恒卉 合著 《可洪音義》與佛典校勘專題•序言
107學年第2學期,萬金川教授於博士班開了一門「佛典目錄版本學」,課程中首先藉由呂澂先生的〈宋藏蜀版異本考〉[1]為切入點,探討了諸刻本藏經的源流與傳承。學界一般將這些藏經分為三系,即屬於北方系的契丹藏,屬中原系的高麗藏初雕本、再雕本、金藏,以及屬南方系的浙本思溪藏、磧砂藏,閩本崇寧藏、毗盧藏。呂氏的觀點認為刻本系統藏經都有一個共同的祖本,是以《開寶藏》不同時期的修訂本(淳化、咸平、天禧、熙寧、崇寧本)為底本進行刊刻;而李際寧、李富華、何梅等[2]則認為三系藏經是分別依照四川、中原、福州三地的不同寫本刊刻而成。
[1] 呂澂〈宋藏蜀版異本考〉,收於《圖書月刊》第2卷第8期,中央圖書館發行,1943年2月,頁3-7。
[2] 李際寧《佛經版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李際寧《漢文大藏經研究論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
釋知如 《可洪音義》所出〈《出曜經.念品》音義〉之校勘
本文立足於衣川賢次、萬金川二位前輩的理念與方法,選擇一部與《法句經》關係密切的譬喻經典——《出曜經》為題材,以《聖語藏》寫本和中原系、南方系刻本皆存之〈念品〉為範圍,校勘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對該品所出之詞條,同時也以可洪所出之詞條或語段來校勘寫本與刻本藏經,對於校出的異文不僅僅「校其異同」,更嘗試「定其是非」,期能藉由彼此互校,相得益彰。
文中首先說明《出曜經》經題之義涵與其在經錄中記載之情形,接著考察本經於寫本和刻本藏經中保存的現況,並略述學界對於《出曜經》的研究概況,進而展開洪書〈念品〉詞條之校勘,最後透過校勘所得進行異文類型分析,嘗試對呂澂所推斷之《開寶藏》在不同時期可能有不同內容的印本,且很可能是中原、北方、南方三系藏經共同祖本之觀點與以檢核,作為判斷三系源流之間關係的依據。
-
釋慧法 《四分律》尼戒前二篇校勘及異文類型分析-以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所出詞條為主(上)
音義書在整體佛教典籍中頗具特殊意義,是中國僧侶在披覽、閱讀藏經時,摘取經文中較冷僻的字詞後,對其形、音、義進行的解說,為古代閱藏的工具書;是中國傳統小學與佛教藏經結合的產物;是「佛教中國化」的一種學術實踐。正是由於其中、印學術結合的特性使得音義書在佛典校勘中具有他類文獻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長期以來音義書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又音義書中,當前學界對於可洪在五代時期完成的《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較之玄應、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其本身卻具有更大的價值,卻受到更少的關注。因此本文就將嘗試在對《可洪音義》所出《四分律·第廿二~廿三卷》的詞條進行校勘的基礎上對《四分律》比丘尼戒前二篇進行校勘與異文類型分析。文章首先以《高麗藏》再雕為底本進行《四分律》相關戒條的全文錄文;其次對《可洪音義》所出詞條以及《四分律》相關戒條進行本教、對校、他校、理教;之後在對二者分別校勘的基礎之上,著重以《可洪音義》對《四分律尼戒前二篇》進行校其是非,勘其異同的比對、說明、整理;最後將校勘後的異文進行匯整與分析,分別列出四種不同的異文類型,以此來管窺刻本藏經諸系統。
-
釋慧法 《四分律》尼戒前二篇校勘及異文類型分析-以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所出詞條為主(下)
音義書在整體佛教典籍中頗具特殊意義,是中國僧侶在披覽、閱讀藏經時,摘取經文中較冷僻的字詞後,對其形、音、義進行的解說,為古代閱藏的工具書;是中國傳統小學與佛教藏經結合的產物;是「佛教中國化」的一種學術實踐。正是由於其中、印學術結合的特性使得音義書在佛典校勘中具有他類文獻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長期以來音義書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又音義書中,當前學界對於可洪在五代時期完成的《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較之玄應、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其本身卻具有更大的價值,卻受到更少的關注。因此本文就將嘗試在對《可洪音義》所出《四分律·第廿二~廿三卷》的詞條進行校勘的基礎上對《四分律》比丘尼戒前二篇進行校勘與異文類型分析。文章首先以《高麗藏》再雕為底本進行《四分律》相關戒條的全文錄文;其次對《可洪音義》所出詞條以及《四分律》相關戒條進行本教、對校、他校、理教;之後在對二者分別校勘的基礎之上,著重以《可洪音義》對《四分律尼戒前二篇》進行校其是非,勘其異同的比對、說明、整理;最後將校勘後的異文進行匯整與分析,分別列出四種不同的異文類型,以此來管窺刻本藏經諸系統。
-
林恒卉 《本事經》〈卷三〉之校勘-以初金再思磧新諸藏經版本暨可洪、慧琳音義等之考察
本文主要以韓僧守其新《新雕校正別錄》中,所指出《本事經˙卷3》中的四處訛誤進行初金再思磧《高麗初雕、金藏、高麗再雕、思溪、磧砂》等藏經刻本之校勘,再輔以《可洪音義》與《慧琳音義》等音義本之他校。為了釐清訛誤,本文也將《本事經˙卷1-3》每卷經文的結構做了表格分析。在《新雕校正別錄》中,守其所指訛誤主要在於重寫之內容,不禁令筆者推敲著訛誤之因素,關於訛誤始見於初高麗《初雕》及金《金藏》之中,那麼是在《開寶藏》開雕時就已刻入?還是《初雕》時訛入?因此《金藏》承其誤?還是抄(寫)手?刻手?版本等其他之問題嗎?……本文首先透過日本《聖語藏》天平寫本(公元740)與初初雕金金藏再再雕思思溪磧磧砂藏等刻本對校之後,也確認了沙門守其所指訛誤之實,但仍有不盡其全面之處,將於本文中論及;同時根據了音義書的他校,也發現了沙門守其在校勘版本上的一些問題,似乎也印證呂澂先生所判定的蜀版有五種版本之說,此乃本文之價值所在。另外,從寫本到刻本,跨越了時空一窺歷代以來,關於藏經勘刻與校勘的種種現象。
-
-
2020-09-25 出版第94期
-
梅靜軒 修持與療癒之間:六朝隋唐之佛教醫療實踐初探
本文從宏觀的角度嘗試梳理漢傳佛教脈絡下的「佛教醫療」所可能涉及的議題,透過學界研究概況的回顧希望能掌握此研究課題發展現況。理論部分依傳統百科全書式的思維,嘗試從漢譯佛典中歸納其中所傳達的身心與存有的本質、生死的流轉與超克,並以此作為一種內部觀點的呈現,也作為本文討論漢傳佛教中的修持與療癒實踐的思想基礎。此外也嘗試從戒律持守下的醫藥使用規範以及禪病療法兩個子題來初步探索僧人修持過程中面對切身健康議題的因應之策。透過文獻梳理,期盼能引發更多青年學者對此主題的研究興趣。
-
屈大成 六群比丘再評價:以漢譯「根有部律」為基本資料
六群比丘是佛教史上頗惹爭議的人物,他們既通世情佛理,又屢屢違犯,令佛一再制戒。在律藏的敘事中,他們是多條戒的引發者,有些事蹟頗富戲劇性,故為不少佛學論著提及。傳統多以六群是惡比丘,近世學人轉而視六群的行徑為方便施設,務令律制變得更完備。而在眾律藏中,惟「根有部律」清楚舉出六群的身分,包含更多的相關記載。本文以漢譯「根有部律」為基本資料,全面舖述六群的行事和行徑,指出六群出身釋種,出家後仍不脫豪門習尚,耽於逸樂、多求利養、惡口傷人,低貶和騷擾同修,既自大又自卑,實為某一類「惡比丘」的典型,不宜以「方便」為由作開脫。
-
楊惠南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135首~第150首
日治時期的古典佛詩,由於台灣已經淪為異國殖民地,再加上由日本間接輸入的西方民主開放的思潮,以及「祖國」(清國)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等等的隔岸呼喚下,台灣佛詩又恢復了詠史的特色,同時也含有「逃禪」的意味。但這一階段的「逃禪」性格,與第一階段的明清時期不同。這一階段的「逃禪」詩,作者本身少有「逃禪」者;而是對明鄭時期「逃禪」者,例如對沈光文、李茂春等人的悲憐。
-
-
2020-06-25 出版第93期
-
蔡耀明 《中論・觀時品》時間哲學之研究
本文以龍樹《中論.觀時品》就時間之考察為主要依據,鋪陳其論題、論旨、與論理方式,從而展開時間哲學之論究。《中論.觀時品》指出,時間概念並非可單獨且客觀存在,而是依存於其它概念且活躍在一套概念群的共構系統。同樣地,就時間向度所做成的分段,例如,過去、未來、現在,也都不是單獨而客觀地存在,而是有賴於不同分段彼此的觀待。人們的時間觀念若無視於時間有關概念群的共構與觀待,其時間觀念將經不起檢視,而淪為謬誤之見。而開發時間之智慧的前提之一,即在於認知且排除時間謬見。
-
楊志常 註釋傳統重建的多重面相-以晚明《成唯識論》註釋傳統的重新建構為例
由於過於強調傳統的正統性和延續性,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現象—晚明的唯識註釋家如何重新建構一個已經中斷的《成唯識論》註釋傳統,一直沒有得到學術界適當的重視和研究。而且目前僅有的少數晚明唯識學相關研究,也止於指出,「性相通融」是此時期唯識學的最大特色。只是,具有「綜攝」意含的「性相通融」一詞,到底代表什麼意義,可能因人而有完全不同的想像,也可能給人一種過於簡化以及同質化的印象。同樣地,「綜攝」一詞,是否是一個定義清楚而且有效的宗教的概念,也曾經引起許多學者的爭論。
藉由有關宗教「綜攝」和「綜合」的文獻討論,本論文首先澄清「綜攝」和「綜合」的差別。接著,透過檢索「性相通融」的出處,以及考察晚明《成唯識論》註釋傳統重新建構的歷史事實,筆者認為,就算晚明《成唯識論》註釋傳統的重新建構有所謂「性相通融」傾向,該傾向也不是「綜合」而是「綜攝」。只是,「性相通融」和「綜攝」都過於籠統,而且傳統建構的可能綜攝範疇也大於「性相通融」的範疇。所以,本研究特別藉用五個晚明《成唯識論》註釋傳統的實際案例來呈現,在實際操作中,傳統重建的多重可能面相。此多重可能面相反映了晚明《成唯識論》註釋傳統的可塑性和時代性。 -
楊惠南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121首~第134首
日治時期的古典佛詩,由於台灣已經淪為異國殖民地,再加上由日本間接輸入的西方民主開放的思潮,以及「祖國」(清國)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等等的隔岸呼喚下,台灣佛詩又恢復了詠史的特色,同時也含有「逃禪」的意味。但這一階段的「逃禪」性格,與第一階段的明清時期不同。這一階段的「逃禪」詩,作者本身少有「逃禪」者;而是對明鄭時期「逃禪」者,例如對沈光文、李茂春等人的悲憐。
-
-
2020-03-25 出版第92期
-
黃柏棋 未生冤已成:當為政治與宗教隱喻之阿闍世
摩揭陀的阿闍世是阿育王之前古代印度最有權勢的國王。本文討論阿闍世王在早期印度思想史上所涉及的一些問題。論文先從初期印度政治體制蛻變來探討摩揭陀國之興起,接著再探究婆羅門跟沙門文本皆出現阿闍世的意涵。再來更進一步檢視社會關係之改變如何促成沙門與國王的結合以及佛陀時代宗教倫理思潮。文章最後以經文及佛音對阿闍世王弒父後心理創傷之批註當為佛陀對此一事件所加評論之註腳。
-
屈大成 從漢譯「根有部律」看古印度佛寺的建築與布局
寺院是僧眾之所居,也是在家人朝聖的場所。寺院的建築、設施、布局等,某程度上可反映出僧眾的日常活動以及其跟俗世交往的情況,亦牽涉到戒律威儀的制訂。在漢譯各派律藏中,「根有部律」約二世紀成書,篇幅廣大,其中提到多種寺院建築,包括門樓、香臺、僧房、供侍堂、禪堂、食堂、浴室、溫室、厨廁、洗足洗鉢處、庫、供病堂、燃火堂、貯水堂、涼室、經行處、壇場、塔、制底、中庭、簷等。本文除總論寺院的名目、規模外,還逐一分述這些建築,最後配合考古發掘及其他文獻記載,提出一些觀察,望有助進一步了解公元初年佛教僧眾的生涯和日常活動。
-
楊惠南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101首~第120首
日治時期的古典佛詩,由於台灣已經淪為異國殖民地,再加上由日本間接輸入的西方民主開放的思潮,以及「祖國」(清國)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等等的隔岸呼喚下,台灣佛詩又恢復了詠史的特色,同時也含有「逃禪」的意味。但這一階段的「逃禪」性格,與第一階段的明清時期不同。這一階段的「逃禪」詩,作者本身少有「逃禪」者;而是對明鄭時期「逃禪」者,例如對沈光文、李茂春等人的悲憐。
-
-
2019-12-25 出版第91期
-
萬金川 《金藏》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毗沙門天王經》對勘
「趙城金藏」之名,若是僅就該一藏經的發現地點來說,這個名詞本身並無問題。然而,若是將「趙城金藏」一詞所指涉的對象視同《金藏》來看,或許就有商榷餘地了。事實上,從版本學的立場來說,存世的《金藏》是由四種刷印時間前後不一,而所依經版或新或舊的印本所構成的。這四種印本分別是「興國院本」、「天寧寺本」,「大寶集寺本」與「廣勝寺本」。此中,真正可以稱之為《金藏》的,其實只有「興國院本」與「天寧寺本」。至於「大寶集寺本」與「廣勝寺本」,則是元代初年大肆修繕《金藏》原初版片之後的刷印本。換句話說,若是就彼此所依版片的修補與否來看,則「大寶集寺本」與「廣勝寺本」或許都只能算是《金藏》的元代遞修本或配補本。由於《金藏》的「興國院本」與「天寧寺本」,今日倖存於世者不足二十卷,而元代刷印的「廣勝寺本」中,卻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卷帙是出自入元之後的補版。儘管學者之間的研究曾經指出,元代的補版工程頗為草率;然而,令人稍感遺憾的,這些研究之中只有極少數是建立在印本之間的詳盡對勘上面。本文將以《毗沙門天王經》為例,透過逐張逐行的印本對勘,而嘗試查明該一經本的金代原刊本及其元初修補本之間,是否有其重大差異,並且也嘗試去說明這種差異的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意義。
-
釋堅融 《中部》後置式關係句的形式、功能與漢譯現象
關係子句是梵、巴佛典中廣泛使用的文句類型,但古漢語卻沒有關係代名詞可與之對應。古代譯師翻譯關係結構時,如何連繫子句與主句乃至處理各小句之間的綰合?囿於篇幅,本文以巴利契經《中部》及其對等漢譯本為研究範圍,探討巴利後置式關係句的形式、功能與其漢譯現象。鑑於巴利語和漢語兩大語言系統的特性差異,本文分別從兩個方向開展論述:一、以類型學理論所建構的關係子句型態分類為基準,兼論巴利語法書的界定,描寫後置式關係句的形式特徵與功能;二、考述《中部》對應漢譯本關係句的語法現象。
諸多經句顯示:古譯師一般都儘量仿照原語的語序來迻譯關係句,形成「向右分枝」的漢語構式。此一處於右分枝的關係子句通常用以提供主題成立的附加或斷定信息。相較於巴利語,一個漢語句子無法容納過於繁複的語句成分。譯師在仿譯關係子句置後的基本樣式下,受到向右分枝的結構影響,漢譯本應運而生一項構句變異,即:從中插入佛典常見的虛設發問「所以者何」或「何以故」。「一個關係句」據此整體擴展成三段式結構,進而顯示漢譯佛典獨特的關係化策略。 -
楊惠南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50首~第100首
日治時期的古典佛詩,由於台灣已經淪為異國殖民地,再加上由日本間接輸入的西方民主開放的思潮,以及「祖國」(清國)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等等的隔岸呼喚下,台灣佛詩又恢復了詠史的特色,同時也含有「逃禪」的意味。但這一階段的「逃禪」性格,與第一階段的明清時期不同。這一階段的「逃禪」詩,作者本身少有「逃禪」者;而是對明鄭時期「逃禪」者,例如對沈光文、李茂春等人的悲憐。
-
-
2019-09-25 出版第90期
-
釋厚觀 《大智度論》無生法忍之探究
《大智度論》將菩薩道的歷程分成「般若道」與「方便道」,「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而得「無生法忍」,正好立於「般若道」與「方便道」的中介點。若此時放捨度眾生願而急入涅槃,便與二乘無異;若能進一步不忘本願,增強慈悲心,致力於淨佛國土、成熟眾生,將來便有可能圓成佛道。
「無生法忍」的內涵是什麼?應如何修學才能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忍菩薩與二乘的「智慧、斷惑」有什麼異同?得無生法忍菩薩是否有欲入涅槃的危機?或是得無生法忍一定能得佛授記將來必定成佛?《大智度論》中存有各種異說,筆者試著加以彙整並予以解說會通。
-
楊惠南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從明鄭到日治時期第1首~第20首
明鄭時期古典佛詩的特色,除了諷頌頹亡之鄭成功王朝的詠史詩之外,最大的特色就是「逃禪」。所謂逃禪,就是把佛門當做躲避戰亂的場所。寫這些詩的詩人,不管是出家僧人或在家居士,都以逃禪的心態來寫佛詩。而清朝的台灣古典佛詩,由於政局已經安定,對於明鄭王朝和唐山故國已無眷戀的情形,因此相關詩詞多屬詠景或抒發一己之情的純粹文學作品。筆者曾在一篇討論台灣古典佛詩的論文──〈明清時期台灣佛寺詩詞的幾個類型〉當中,說到明鄭乃至清朝的古典佛詩,可以分為下面幾個類型:(1)「逃禪」類;(2)詠史類;(3)純文學類。其中,詠史類又細分為兩種:(1)以嘲笑、譏諷的語氣詠史;(2)以平實或同情、悲憫的語氣詠史。前者如嘲笑朱一貴事件和林爽文事件;而後者則大體以鄭成功王朝的興衰,做為吟詠的對象。
-
Bhikkhu Anālayo On the Six Sense-spheres(3)-A Translation of Saṃyukta-āgama Discourses 250 to255
-
-
2019-06-25 出版第89期
-
林恕安、胡志強、耿晴 合著 佛教意識哲學專輯・導言
意識研究是當前蓬勃發展的跨學科研究,涵蓋認知科學、腦神經科學、心理學、哲學(英美分析哲學、歐陸哲學、佛教哲學)等等,主要研究何謂意識?什麼是有意識的心理狀態?何謂自我意識、我們一定有自我意識嗎?意識有哪些性質?意識如何可能、腦神經科學能夠說明意識嗎?意識有什麼功能(為何我們需要意識)?以植物人為例,以上的研究將會決定我們如何判斷植物人是否有意識,就什麼意義、面向而言來判斷,並且如何考量其是否可能恢復意識,以及如何讓其恢復到有意識的狀態,這也牽涉到相關的倫理議題。又例如目前愈來愈火熱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議題,機器是否可能有意識,抑或意識為人類所獨有。
就佛教而言,北美認知科學對禪修作了不少實驗研究,也定期與佛教界對話,心理治療也開始融和一些正念或禪修的技巧。禪修有其實務成果,不需科學的驗證,然而透過科學研究與對話,有助於我們更瞭解大腦與意識。也就是說,佛教的禪修不僅作為宗教修練而已,也能就理論與實踐層面提供不同的視野與思想資源。
本專輯的規劃,嘗試從佛教的傳統來呼應當前學界對於意識研究的重視。本導言分為以下兩個部分。首先簡要回顧當前英語學界關於佛教意識哲學的主要議題與研究現況,其中也包含對於本專輯中三篇論文背景脈絡的簡介。其次,以關於佛教意識哲學之主要特色與未來待探究之議題幾個大方向的觀察作為總結。 -
耿晴 意識如何緣取不存在的對象?:以經量部上座的理論與說一切有部眾賢的批評為中心
本文旨在檢討佛教阿毘達磨哲學之經量部論師上座關於「意識如何緣取不存在的對象」的理論,以及來自於說一切有部論師眾賢的批評。不同於有部三世實有的形上學立場,在經量部剎那滅的形上學前提下,上座必須面對不存在的對象如何能夠引生意識的困難。本文集中探討意識緣取不存在的對象的三種案例:(1)緊接眼識後生起的意識如何緣取已經不存在的外在對象?(2)意識如何回憶?亦即意識如何緣取久遠過去曾經歷的對象?(3)意識如何緣取過去未曾經歷或未來的對象。在這三種案例下,分別檢討上座解決困難的策略,以及如何招致來自眾賢的批評。本文贊成眾賢對於上座理論的批評,但進一步主張,對於經量部來說不可解的困難卻也構成了佛教知識論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在上座之後,以陳那為代表的認知二分說—認知中帶有對象的影像—能夠成功地回應來自於眾賢的批評。
-
胡志強 護法《成唯識寶生論》論知覺及其所緣:兼與當代理論之交涉
護法《成唯識寶生論》是世親《唯識二十論》的重要註釋書。按照護法的詮釋,《二十論》的開頭先引經證、而後立量理證,其中瞖眼人的知覺是論證中的重要實例(喻依),瞖眼人的眼識有如同毛髮等物一樣的顯現,然其所見的毛髮等物是不存在的。對瞖眼人此例,《寶生論》中的論敵給出一實在論的因果說明,認為是透過白色網膜縫隙的光明分造成瞖眼人見髮的錯覺,瞖眼人的知覺並非沒有外境。對此質疑,護法訴諸陳那在《觀所緣論》中提到的所緣(ālambana)(認識對象)的二個條件來批評論敵。作為所緣的必要條件之一(C1),就是要在感官識中顯現,亦即感官識要有所緣的相(ākāra)。所緣的必要條件之二(C2),就是具有讓認識(對該所緣的知覺)生起的因果作用。護法認為,即便設許論敵的說明符合C2條件,但因缺乏C1條件,因此瞖眼人所緣並非外境。針對餓鬼們同見膿河的例子,雙方也有類似的交鋒。
分析護法論證的合理性的策略之一,是與當代議題交涉或對話。大致上我們可以說,當代知覺因果論(the causal theory of perception)的基本要點類似於前述之所緣二條件C1與C2,不僅如此,知覺因果論者均同意,在某人X面前沒有某事物Y時,對X而言看起來好像有某個Y仍是可能的,如同世親與護法所言,前面沒有髮、膿河,仍可能有髮、膿河的知覺經驗。也就是說,非正常知覺與正常知覺可具有共同要素(例如顯現),此點正是支持實在論的非此即彼論(disjunctivism)所極力反對的。本文對非此即彼論提出嘗試性的批評,以支持護法與知覺因果論。 -
林恕安 從三性的批判談清辨對無分別智的主張
清辨 (Bhāviveka, 500-570 A. D.)一般認定活躍於六世紀,與當時最負盛名的瑜伽行派學者護法 (Dharmapāla, 530-561 A.D.)、安慧 (Sthiramati, 510-570 A. D.) 等同時代。他承襲著中觀一貫否定式的路徑而認為即使對於「勝義空」這樣的概念也不可執實,方能達到遠離二邊的中道;然而與清辨對辯的瑜伽行派不但認為「無分別智」(Tib. : rnam par mi rtog pa'i ye shes; Skt.: nirvikalpa-jñāna) 以真如 (tattva) 作為對象,且「無分別智」也是修行要達到的境地。雖然兩派的爭論已有一些相關的研究,但對於清辨如何看待無分別智的部份則較少著墨。由於無分別智的樣態不可能脫離各自的修證脈絡,本文將從三性 (trisvabhāva) 的對辯說明清辨對無分別智的詮釋與主張,既然他不承認真如所緣,是否也因此主張無分別智不存在?但如果他主張無分別智存在,則無分別智認知的對象究竟又會是什麼呢?
-
-
2019-03-25 出版第88期
-
釋厚觀 正性離生、菩薩位之探究
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及《大智度論》中常見「菩薩位」之語詞,對照玄奘譯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則作「菩薩正性離生」。「菩薩位」是特指菩薩修行歷程中特殊的一個階位,入菩薩位之後,將決定趣向於無上菩提而成佛;「菩薩地」則是泛指菩薩從初發菩提心到成佛之間菩薩修行的所有階位,二者用法不同。
「入菩薩位」後,行者將畢定成佛,因此,如何才能入菩薩位成為一重要的課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及《大智度論》中提到了多種不同的方法,有的說「觀空入菩薩位」,有的說「行般若波羅蜜入菩薩位」,有的說「應行六波羅蜜方能入菩薩位」,有的說「要兼具般若波羅蜜與方便力才能入菩薩位」,也有說「要遍學聲聞道、辟支佛道、佛道,再以菩薩的道種智入菩薩位」,更有說「要具足發意、修行、大悲、方便等四法方能入菩薩位」。
由於入菩薩位應具備的德目說法不一,所證得菩薩位的階位高低也不盡相同。如以「無生法忍」為基準,有的菩薩位比「無生法忍」低一些,有的則在「無生法忍」之上,必須依前後文才能判斷,不能一概而論。筆者試著整理《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及《大智度論》之種種異說,希望藉此能正確掌握「菩薩位(菩薩正性離生)」的完整樣貌。 -
Bhikkhu Anālayo On the Six Sense-spheres (2) — A Translation of Saṃyukta-āgama Discourses 230 to 249
本文為《雜阿含經》英譯系列論文的第八篇,前面七篇已發表在《法鼓佛學學報》11-17期。
鑑於漢譯《雜阿含經》(T 99)尚未出現完整的英譯,此為歐美學者閱讀、研究或引用此一漢譯文獻的障礙;此一系列論文的英譯、註解及比較研究應可減低這樣的隔閡。
對漢語世界而言,此一系列的英譯可以當作經文的白話翻譯,可以參考當代的《雜阿含經》白話譯本而取長捨短,部分註解可以用來追溯可能的巴利用字,並參酌巴利註釋書的字義解釋。相關的論文不僅提示漢巴對應經典之間主要的差異,也徵引了部分梵文殘卷與寂止天(Śamathadeva)的《俱舍論附隨・疏》(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所抄錄的《雜阿含經》經文。 -
林 隆嗣著 釋洞崧 譯 上座部大寺派與無畏山派裡頭陀支的解釋 ——關於《解脫道論》的所屬部派
覺音在其《清淨道論》(Vism)與其他巴利註釋中提到匿名的非正統見解,而法護則有時在其複註中確認這些人為「無畏山住者」(Abhayagirivāsin)。研究指出,這些見解被發現出現在《解脫道論》(Vim)中,而因此《解脫道論》被視為是此派系的作品。儘管如此,有的學者對於以下三點一致之相關性提出質疑,也即是:那些覺音所知道的匿名者之見解,法護的確認,以及在《解脫道論》中的教義。然而,若是聲稱某個理論證據不足,而基於一連串的缺乏確證與進一步的考證的假設,卻又沒有反證,而據此嘗試作出選擇性的解釋,這似乎有欠公平。需要更仔細考量的是:如果一個構成元素的法(dhamma)不同的話,則它將影響整個上座部阿毘達磨哲學精密系統的基礎。就此意義,頭陀(苦行)在阿毘達磨分類中被賦予的地位,在作為辨識無畏山住者的一個標準而言,可以說是極具意義。
考慮到這一點,我重新檢視在Vism與Vim對於頭陀dhutaṅga定義的爭論,然後考慮如何以及為何大寺派住者(Mahāvihāravāsin)以及無畏山住者(Abhayagirivāsin)會將之(頭陀)歸類至不同【p. 31】的種類。若概觀在《清淨道論》與《解脫道論》的資料,尤其是仔細關注《解脫道論》裡的文句「此〔頭陀〕不應說善、不善、無記」的話,則可質疑其對應性。但是,有個更關鍵的證據將Vim聯繫至無畏山住者,那就是Vim在概念(paññatti)的序列中清楚地提到頭陀,而這點則為多數的學者所不知。
若再更深入觀察巴利聖典,我們則經常看到那些惡欲、追求名聲等頭陀修習者。而且,對於頭陀的理解,也可以看出在Vism與巴利註釋出現哲學上的差距。再者,我們留意到在《清淨道論》頭陀的定義並給出自覺音,而是引用自作為古老註釋的義疏(Aṭṭhakathā)。這似乎可以合理來推測:對於頭陀的討論曾發生在巴利註釋的錫蘭資料與暗誦者(bhāṇaka),而這兩個學派各自建立其頭陀的定義,在接受之前所討論的同時,試著否定頭陀可以是不善的見解。
-
-
2018-12-25 出版第87期
-
蔡耀明 觀世音菩薩之當代繼承與闡揚:以時空向度與宗教文化遺產為視角
本文從活在當代與立足當地出發,解明如何繼承與闡揚觀世音菩薩之宗教文化遺產。雖然活在當代與立足當地,透過時間向度與空間格局的解開,即不必自限於一時一地。以宗教文化遺產為著眼,並且以佛教弘化學為考量,繼承與闡揚觀世音菩薩之宗教文化遺產,經由正確的認知與適當的精進,即可接通觀世音菩薩帶頭開創的事業,以個體與群體的方式落實且推動在佛教修行道路的進展與提昇,以及幫助廣大且多樣的眾生減輕與脫離世間的各種困苦。
-
李周淵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經題考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T362)翻譯於西元3世紀中期之前,是現存漢譯佛典中最古老的淨土經典。長久以來,此經經題的意義一直少人探討,而解讀此經題最大的困難在於音譯詞「薩樓佛檀」。
首先,西元515年左右成書的《出三藏記集》所記載的是「薩樓檀」,而西元700年左右成書的《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記載的則是「薩樓佛檀」,因此在解讀經題時,需要考慮有這兩種不同的情況。
其次,本經的原典語言,很可能是印度的俗語,根據本經的其他用例、印度語音演變的規則以及初期漢譯佛典梵漢對音的規則,可以構擬「薩樓(佛)檀」所對應的梵語是*th/s...l/r/ṭ/ḍ/d...d/t...的形式。
最後,從以上成果出發,提出一種相對合理的可能性,即「薩樓檀」所對應的梵語是sarvalokadhātu(一切世界),而經題「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檀過度人道」對應的梵語接近於*amitābha-samyaksaṃbuddha-sarvalokadhātu-manuṣya-parimocaka,是多個佛陀稱號的並列,大意為「救濟一切世界人類之正等正覺阿彌陀佛」。 -
蘇錦坤 《法句經》(T210)的詮釋與翻譯-以法光法師《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為例
本文簡介法光法師的《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一書,並提供幾個評論,作為將來T210《法句經》完整翻譯的參考。此書有許多相當突出的論點,例如:
1. 指出前人的英譯,常有依照巴利《法句經》的偈頌字句來翻譯漢譯《法句經》的現象,這種翻譯方式會遺漏、遮蔽漢譯文本的「版本」特性。
2. 提出扎實的例證,認為「核心26品」中至少有些偈頌不是出自巴利《法句經》;有些偈頌的譯詞顯示其原始文本(Indic text)的語言可能既不是巴利(Pāli),也不是梵文(Sanskrit)。
3. 提出一個「說帖」,試圖解說《法句經》未編入四阿含或四部尼柯耶的原因。
4. 完成「核心26品」的英譯,並且在註解裡編列了各首偈頌的巴利、梵文、犍陀羅、藏文或波特那《法句經》的對應偈頌,同時也有詳盡而參考價值極高的附註。
5. 當T210《法句經》的用詞與巴利《法句經》不同時,常有學者輕易地判讀為支謙的誤譯,作者在「多文本的偈頌比較研究」之下,證實漢譯確實另有所本。
本篇就「英譯商榷」、「校勘與『訛字』」、「『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等三點對該書作評論。
-
-
2018-09-25 出版第86期
-
釋厚觀 從《大智度論》看〈發趣品〉的十地思想
《大智度論》提到三類「十地」的內容,一、乾慧地等共三乘的十地,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發趣品》中無名字的菩薩十地,三、歡喜地等菩薩十地。其中《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發趣品》中無名字的十地列舉了各地菩薩應修學的德目,日本學者神林隆淨教授認為這些德目毫無次第,只是雜亂的羅列而已。
筆者試著從《大智度論》的釋論,先分析各地菩薩應修學的德目內容,再將該地的相關的德目組織、關連,最後再探討十地之間的關連。結果發現:有些字面上看起來類似的德目,但前後各地還是有淺深不同;有些修行德目在字面上看起來與聲聞經所說的行法沒什麼不同,但其實菩薩的心境與聲聞差異甚大;有些德目在字面上雖然不同,但都表達同一意趣,如二地所說的「持戒清淨」,三地的「住慚愧處」,四地的「不捨阿蘭若住處」,六地的「不作聲聞、辟支佛心」,都是表達「勿起二乘心」的意趣。綜合起來觀察,各地的行法其實都包含有「對治煩惱、缺失」與「悲智不斷增上」的作用,可提供學人進階菩薩行的指南。
此外,《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發趣品》說「第十地當知如佛」,為何《大智度論》卻提出「第十地當知如佛」或「第十地即是佛地」等二說?又《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發趣品》中「無名字的菩薩十地」與「乾慧地等共三乘的十地」、「歡喜地等菩薩十地」之關係錯綜複雜,本文試著提供一條解析的線索。 -
屈大成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研究史回顧──以成書年代為中心
中土佛教一向推崇《四分律》,「根有部律」則備受忽視。反觀西方學界,自十九世紀中葉始,已注意到「根有部律」的重要性,其後通過對文本的細讀、跟其他律藏和印度法典作比對,以及運用碑銘、雕像,寺院遺跡等出土文物相印證,發掘出其中的古舊記載,並把「根有部律」的成立年代大大推前,對探討古印度的佛寺組織、僧尼規範,有莫大意義。本文縷述西方學界有關「根有部律」成立年代的討論,尤詳述Gregory Schopen這富顛覆精神的佛學者的看法,期望能喚起漢語佛學界對「根有部律」的重視。
-
林 隆嗣著 釋洞崧 譯 在巴利註釋文獻裡sacca的分類—與《解脫道論》之比較
-